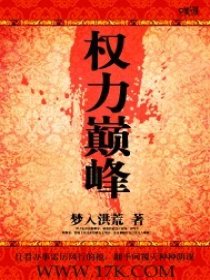:第一章
张来福上初三的时候,老师布置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他在文章里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
等到他升高三时,他选择了上文科班。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上文科是为了考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作家呀!
也就是说,张来福的人生理想在中学时代就很固定,就很执着,也很自信——
就是想当一名作家。
然而高考他落榜了。分数差得不多,十小几分。于是,到县城复读。
然而,复读一年,高考又未中。他懵了。
他父母也懵了。
那天上午坏消息传来,张家顿时坠入愁云惨雾。
李红霞放下缝纫活儿,躲到房间里掩面哭泣。张国平坐在堂屋门槛上对着院子抽烟,神态木然,活像一尊泥胎菩萨。
当他站起身走向猪圈去小便时,邻居家常来串门的虎斑猫不知趣地绕着他的裤管大献妖媚,他“咄!”一声赤脚踢去,却精准地踢在梨树干上,震下一只青梨来。
他跌坐在地,捧着血淋淋的翻掉半块趾甲的脚丫倒抽凉气。跟着,出人意料地捡起地上的梨子,揩也没揩就啃起来,大啃特啃,啃得汁液横飞,啃得泪水滚落。
但张国平却仍没有去责备儿子。
张国平的母亲一辈子生了七个儿子,前六个都夭折了,只剩下他这根独苗,在父母呵护下居然一路上学考上昭阳师范,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结婚后妻子在生下儿子第二年得了一场大病,动手术后竟从此不能生育,结果儿子又成了一株独苗,成了全家的心肝宝贝。
现在心肝宝贝第二次高考落榜,他怎么忍心给他的心情雪上加霜呢?他要妻子顿顿把饭菜端到儿子房间里,这小子吃过了饭碗一推倒又上床睡觉了。
直到第三天中饭后,他才走进儿子的房间,轻言悄语地说了一番下学期继续让他去复读的决定。
张国平的决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位资深的语文教师,现在又调回本庄初级中学当了副校长,自已教过的不少学生都能考上大中院校跳出了农门,却不能培养出自己的独生儿子,这叫他情何以堪?!如果儿子天生愚钝也就罢了,恰恰相反,他打小就聪明过人,只不过贪玩一点罢了,任性一点罢了。
即便今年差了十七分,也没有大不了的,再让他复读一年,自己再盯紧一些,明年就算考不上本科,上个大专决计不会有问题的。
儿子今年也才二十岁,明年上大学一点儿也不迟!
想不到儿子却回了他两个字:
“不上!”
张国平终于爆发雷霆,对儿子吼道:
“不上!不上你能干什么?从小到大全家人都疼着你护着你,油瓶儿倒了都不让你扶,你现在不上学是能挑担还是能挖沟?不上?不上你起来给老子放羊去!”
张来福一骨碌从床上起来,径直走进院角的羊棚里,牵出两只山羊,出门扬长而去。
张来福在床上躺了三天,决定不再复读。
他认为像他这样有尊严的人,读“高四”尚可姑且,读“高五”便是耻辱了。
虽然他在城北中学的补习班中不乏“高六”、“高七”的,甚至还有一个号称“八年抗战”的老兄,居从上到“高九”。
如此疯狂复读的情形在农村太寻常了——为了跳出农门脱离苦海拿上国家户口红本本吃上商品粮,哪怕把整个青春消磨殆尽也是值得的。
可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两度高考失利,张来福的耐心已经到了极点。
张来福觉得,现在都一九八六年了,正是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开辟出一条不借助高考而达成的另外的人生成功之途。
想不到父亲竟然拿放羊来要挟他听从安排再度去复读。
“吓唬谁呢!不复读我就成放羊娃啦?”张来福气哼哼地牵着两只山羊出了院门。
他家大瓦房刚建两年,在张家庄最北面,他顺着屋后土路朝西面大河边的小树林走去。
他想这三天躺在床上骨头都散架了,正好出来散散心,透透新鲜空气。家里气氛实在太压抑了,好像自己没考上大学天都要塌下来一样!
庄西的这片林子,占地三四亩,树高叶茂,蓊蓊郁郁。
春天杨花悬满枝头的时候,那贞洁的莹白真的欺霜赛雪,满树林都流动着迷人的馨香。
苦楝开花满树紫,女孩们举着碧绿的芦竹来打,用手帕兜着拿回去,把花瓣中间圆柱形的花柱摘下来,用绣线缀成耳环、手镯和项链戴起来,招招摇摇的,真是可爱啊;而男孩子感兴趣的是结成了葡萄状的楝树果子,那是他们用弹弓打麻雀天然的子弹。
麦黄时节,桑葚成熟了,多得如天上繁星,这才是一年中小树林最喧闹的辰光,孩子们坐在枝丫上信手采撷,大快朵颐,各式雀鸟也麇集于此,翔舞起落,参与争食——这大概是自古以来乡村最经典的景象之一吧!夏日炎炎,孩子们屏气息声踅入林中,是为了用顶端敷着面筋的竹杆去粘知了——也有用麦秸编成的喇叭状套笼去套的;若是捉天牛,总是细心地数它长触须上的白点以判断几岁,真是很愚昧啊;也还有窝起肉掌拍那些锔在光滑树干上面的牛虻的,一只只收藏到火柴盒中,用来做钓鲹鱼的饵料。
到了冬天树林里却相当落寞了,偶尔有人成双捉对踩着月色星光溜进来,总是浑身带着荷尔蒙的腥气,或搂抱,亲嘴,或把老棉袄铺在枯枝败叶之上,做那翻云覆雨的勾当。
离小树林还有几十米,张来福听见里面传出“嘎哦——嘎哦——”的鹅叫声,顿时来了神,拽着两只羊奔过去。
他想肯定是谁家的鹅顺大河游到这边来了,弄得好能捡两只大鹅蛋吃吃哩!
进入树林一看,果然有七八只大白鹅在里面吃草。张来福松开牵绳,两只羊撒着欢儿加入了饕餮之阵。
看到通身雪白同为食草动物的禽畜和谐地搅在一起共同享受,张来福心情大悦。
低头在草丛间寻蛋,却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咳嗽,吓了他一跳,走过去一看,不由乐了。
他看见草地上躺着一个人,身穿着旧巴巴的小褂裤,脚蹬破凉鞋,头发蓬乱,嘴里叼着半截香烟,正在吞云吐雾,活像一个穷困潦倒邋邋遢遢的流浪汉。
在他身后的苦楝树上,斜倚着一根顶端系着红布条的竹竿。
这人叫沈喜宝,是原大队通信员沈国才的儿子,高中毕业学了两年木匠后又重新复读,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又没考中。他已经二十四岁了。
“喜宝,是你在这儿放鹅呀!”
沈喜宝斜睨了他一眼:
“你不也来放羊了么!”
等到他升高三时,他选择了上文科班。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上文科是为了考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作家呀!
也就是说,张来福的人生理想在中学时代就很固定,就很执着,也很自信——
就是想当一名作家。
然而高考他落榜了。分数差得不多,十小几分。于是,到县城复读。
然而,复读一年,高考又未中。他懵了。
他父母也懵了。
那天上午坏消息传来,张家顿时坠入愁云惨雾。
李红霞放下缝纫活儿,躲到房间里掩面哭泣。张国平坐在堂屋门槛上对着院子抽烟,神态木然,活像一尊泥胎菩萨。
当他站起身走向猪圈去小便时,邻居家常来串门的虎斑猫不知趣地绕着他的裤管大献妖媚,他“咄!”一声赤脚踢去,却精准地踢在梨树干上,震下一只青梨来。
他跌坐在地,捧着血淋淋的翻掉半块趾甲的脚丫倒抽凉气。跟着,出人意料地捡起地上的梨子,揩也没揩就啃起来,大啃特啃,啃得汁液横飞,啃得泪水滚落。
但张国平却仍没有去责备儿子。
张国平的母亲一辈子生了七个儿子,前六个都夭折了,只剩下他这根独苗,在父母呵护下居然一路上学考上昭阳师范,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结婚后妻子在生下儿子第二年得了一场大病,动手术后竟从此不能生育,结果儿子又成了一株独苗,成了全家的心肝宝贝。
现在心肝宝贝第二次高考落榜,他怎么忍心给他的心情雪上加霜呢?他要妻子顿顿把饭菜端到儿子房间里,这小子吃过了饭碗一推倒又上床睡觉了。
直到第三天中饭后,他才走进儿子的房间,轻言悄语地说了一番下学期继续让他去复读的决定。
张国平的决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位资深的语文教师,现在又调回本庄初级中学当了副校长,自已教过的不少学生都能考上大中院校跳出了农门,却不能培养出自己的独生儿子,这叫他情何以堪?!如果儿子天生愚钝也就罢了,恰恰相反,他打小就聪明过人,只不过贪玩一点罢了,任性一点罢了。
即便今年差了十七分,也没有大不了的,再让他复读一年,自己再盯紧一些,明年就算考不上本科,上个大专决计不会有问题的。
儿子今年也才二十岁,明年上大学一点儿也不迟!
想不到儿子却回了他两个字:
“不上!”
张国平终于爆发雷霆,对儿子吼道:
“不上!不上你能干什么?从小到大全家人都疼着你护着你,油瓶儿倒了都不让你扶,你现在不上学是能挑担还是能挖沟?不上?不上你起来给老子放羊去!”
张来福一骨碌从床上起来,径直走进院角的羊棚里,牵出两只山羊,出门扬长而去。
张来福在床上躺了三天,决定不再复读。
他认为像他这样有尊严的人,读“高四”尚可姑且,读“高五”便是耻辱了。
虽然他在城北中学的补习班中不乏“高六”、“高七”的,甚至还有一个号称“八年抗战”的老兄,居从上到“高九”。
如此疯狂复读的情形在农村太寻常了——为了跳出农门脱离苦海拿上国家户口红本本吃上商品粮,哪怕把整个青春消磨殆尽也是值得的。
可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两度高考失利,张来福的耐心已经到了极点。
张来福觉得,现在都一九八六年了,正是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开辟出一条不借助高考而达成的另外的人生成功之途。
想不到父亲竟然拿放羊来要挟他听从安排再度去复读。
“吓唬谁呢!不复读我就成放羊娃啦?”张来福气哼哼地牵着两只山羊出了院门。
他家大瓦房刚建两年,在张家庄最北面,他顺着屋后土路朝西面大河边的小树林走去。
他想这三天躺在床上骨头都散架了,正好出来散散心,透透新鲜空气。家里气氛实在太压抑了,好像自己没考上大学天都要塌下来一样!
庄西的这片林子,占地三四亩,树高叶茂,蓊蓊郁郁。
春天杨花悬满枝头的时候,那贞洁的莹白真的欺霜赛雪,满树林都流动着迷人的馨香。
苦楝开花满树紫,女孩们举着碧绿的芦竹来打,用手帕兜着拿回去,把花瓣中间圆柱形的花柱摘下来,用绣线缀成耳环、手镯和项链戴起来,招招摇摇的,真是可爱啊;而男孩子感兴趣的是结成了葡萄状的楝树果子,那是他们用弹弓打麻雀天然的子弹。
麦黄时节,桑葚成熟了,多得如天上繁星,这才是一年中小树林最喧闹的辰光,孩子们坐在枝丫上信手采撷,大快朵颐,各式雀鸟也麇集于此,翔舞起落,参与争食——这大概是自古以来乡村最经典的景象之一吧!夏日炎炎,孩子们屏气息声踅入林中,是为了用顶端敷着面筋的竹杆去粘知了——也有用麦秸编成的喇叭状套笼去套的;若是捉天牛,总是细心地数它长触须上的白点以判断几岁,真是很愚昧啊;也还有窝起肉掌拍那些锔在光滑树干上面的牛虻的,一只只收藏到火柴盒中,用来做钓鲹鱼的饵料。
到了冬天树林里却相当落寞了,偶尔有人成双捉对踩着月色星光溜进来,总是浑身带着荷尔蒙的腥气,或搂抱,亲嘴,或把老棉袄铺在枯枝败叶之上,做那翻云覆雨的勾当。
离小树林还有几十米,张来福听见里面传出“嘎哦——嘎哦——”的鹅叫声,顿时来了神,拽着两只羊奔过去。
他想肯定是谁家的鹅顺大河游到这边来了,弄得好能捡两只大鹅蛋吃吃哩!
进入树林一看,果然有七八只大白鹅在里面吃草。张来福松开牵绳,两只羊撒着欢儿加入了饕餮之阵。
看到通身雪白同为食草动物的禽畜和谐地搅在一起共同享受,张来福心情大悦。
低头在草丛间寻蛋,却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咳嗽,吓了他一跳,走过去一看,不由乐了。
他看见草地上躺着一个人,身穿着旧巴巴的小褂裤,脚蹬破凉鞋,头发蓬乱,嘴里叼着半截香烟,正在吞云吐雾,活像一个穷困潦倒邋邋遢遢的流浪汉。
在他身后的苦楝树上,斜倚着一根顶端系着红布条的竹竿。
这人叫沈喜宝,是原大队通信员沈国才的儿子,高中毕业学了两年木匠后又重新复读,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又没考中。他已经二十四岁了。
“喜宝,是你在这儿放鹅呀!”
沈喜宝斜睨了他一眼:
“你不也来放羊了么!”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