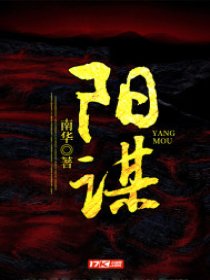:第十一章
八月十六日,张来福迎来了他进厂的第一个周末。
下午下班后就急忙洗澡换衣,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出了农药厂大门。
他要去看沈喜宝,了解他这一周的情况。
不到下午六点,太阳还悬在西天,估计沈喜宝和他的师傅小四子还没收摊,便径直朝南门街而去。
他听小四子说的,刻章的早市、晚市是不能丢的,也就是说,要起早带晚,上班和下班时间街上人流涌涌的,生意概率比较大。
到了那儿,果然两人还在。
小四子正在给一个拎着买菜布兜的老妇人刻章,沈喜宝聚精会神地凑在一边看。
小四子的刻字摊非常简单,就是在香烟纸箱上蒙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几十个各种规格的章料子,一个印油盒和一本收据。
他是无照无证刻章,自然没有发票,要发票只能给收据;另外收据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刻好章后在上面盖给人家看,满意给钱。
摊子前沿倚着一块杂志大的三夹板,上面写着“快速刻字”。
小四子刻私章不用先在章料上写反字,也不用固定夹,直接捏在手上刻,他用的是自制的钢锯条磨成的刻刀,用胶布缠着刀柄,柔中带刚,先打边框,分字格,然后直接刻字。
他刀法十分娴熟,刀尖“噼啪”有声,很快就刻好了,蘸上印油,使劲往收据上一盖,殷红的印章赫然在目。
那妇女点点头,掏出四块钱给他,笑眯眯地走了。
小四子吁了一口气,掏出香烟来,自己叼一根,递一根给沈喜宝,两人凑着脑袋点上,一副师徒乐的样子。
旁过头来,才看见张来福站在一边。
“来福,你怎么来了?”沈喜宝喜悦地叫道。
“对对,今天是周末,我倒忘了!”小四子笑道,赶紧招呼张来福坐下——他用报纸包着两块砖头,供顾客歇脚的;沈喜宝也是坐的这样的“凳”。
张来福接过小四子递过的烟刚点上,沈喜宝便迫不及待地问起他在农药厂的情况来。
“怎么样,苦不苦,还能适应吗?”
“谈不上苦,有力气就行。有什么不能适应的,能适应。”张来福轻描淡写地说,“反正进厂也是过渡,挣够做生意的本钱就出来了。”
反过来问他:“你呢,刻章学得怎么样了?”
“我师傅说我进步快,有悟性哩!”沈喜宝嘻嘻笑,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章料子来,摆在摊子角上,有七八枚之多。
张来福拿来看,原来上面都刻上了字。大多是独体字,如“王”、“玉”、“正”“田”、“日”等;也有简单的合体字,如“明”“林”“杜”、“宝”、“直”等。
虽然笔划粗细不均,还有断裂的,但总体上横平竖直,像小学生认真写下的铅笔字。
“不错,不错!”张来福称赞。
“先从简单的字刻,刻熟了再刻复杂的。”小四子笑着告诉他。
“这些章料子怎么不齐整?”张来福问。
他发现沈喜宝给他看的这些图章长短不均,有的只有本来的一半长短。
“这是磨短的。”沈喜宝抢着解释,“我师傅要我刻了磨,磨了刻,把章料子磨得捏不上手了,基本功也就差不多了。”
“我懂了,同时这也节约实习材料!”张来福嘴里说着,心里却在想:沈喜宝这家伙,二十四岁的高考落榜生,对十八岁的初一都没念完的小四子一口一个“我师傅”,听起来怎么有些别扭呀?可能自己潜意识中还是有些瞧不起小四子。
这是不应该的,小四子对他们多接纳、多热心、多真诚!
不能因为小四子家庭背景比自己差、读书不如自己多和比自己岁数小就产生轻视之心;另外这个时候恃才自傲是可笑的,人家通过做手艺一天能挣几十块钱,你呢?你才是个刚刚上班的临时工!
还有,沈喜宝不称小四子师傅称什么,两人现在本来就是师徒关系——如果现在再喊他“小四子”,那就不上规矩不懂礼貌了。
他对沈喜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你下了大功夫,难怪进步这么快。”
小四子说:“再过一个礼拜,我估计就喜宝就可以出师了。”
张来福笑道:“他学木匠两年,师傅都没教他真功夫,现在跟你学刻章,半个月就能出师了——师傅跟师傅就是不一样啊!”
沈喜宝也跟着讪讪地笑:“是的,不一样。”
“这是应该的么,承蒙你们看得起我,到扬州来投奔我,我也自豪哩!把你们俩安排出来,以后我到了庄上说起来脸上有光哩!”小四子说着,离开小板凳站了起来,指示沈喜宝:“收摊吧,咱们买菜去!”
沈喜宝问:“师傅,不再等个把生意?”
“不等了,来福来了,早点回去弄饭,喝酒!”
晚上照例如同上次一样,借了房东老强家的客厅吃饭,把房客们全部请到。
事后小四子讲,出门在外讨生活,最讲究跟房东房客处好关系,买来的菜三个人也是吃,大家一起也是吃,多几双筷子而已,却多了热闹和亲热;朋友之间是吃来吃去的,今天你喊他,明天他也会喊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是个宝,关键时候少不了。
听了小四子这些靠谱的江湖话,张来福心里感到佩服,好多知识和经验是学校里课本上学不到的,必须亲身体验才能懂得和掌握。
席间老强问了张来福工作情况,张来福一一作了回答,说自己能够胜任,让老强放心。
小陈一喝酒话就多,爱显摆,问大家小白今天晚上穿的这件连衣裙好看不好看。
这小白是泰州苏陈的,跟小陈老乡,在一家茶社上班,只做一顿早市,下午便没事了,不是到老西门小陈摊点上陪着,就是回家钻进楼梯间睡觉,小陈经常笑骂她是个“懒丫头”,人长得像个又白又暄的肉包子。
其实小白是胖得瓷实,胖得健康,简直胖得理所当然,不胖倒不是小白了。
这姑娘喜眉笑眼,没有心机,随你怎么跟她开玩笑都不生气,农村人常说没心没肺的人是“福人”,因为不生气人缘就好,不生气人就不生病,人缘好就四邻和睦,不生病就长命百岁。
张来福的审美层次高,他觉得这样的姑娘也挺好,他喜欢笑眉笑眼一团和气的人。
今晚小白穿了一件簇新的白衣连衣裙,就像一朵盛开的白牡丹,大家都说好看。
听大家都赞扬,小陈乐不可支,告诉大家下午刻了个公章,对方没有介绍信,宰了人家五十块钱,被小白知道了,硬把钱要过去买了条裙子。
“自从跟她谈恋爱,我就落不下几个钱来,又要吃零食又要供衣服——这个败家婆娘!”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老强却正色道:“小陈,我知道你手艺好,但公章这东西我劝你还是不要碰,万一出了事是要坐牢的,到时候恐怕我这个房东都要受牵连!”
小陈说他很小心的,基本都是刻有介绍信的公章,没有介绍信看抬头,抬头太“大”坚决不刻。
他指着小四子说:“上次小四子接了个公章,抬头是公安局,送给我刻,被我骂了一顿——就是给一千块钱也不能刻呀——公安局的章还要找我们野摊子刻么?还没有介绍信!来刻章的分明是个犯罪分子么!”
小四子笑着对大家说:“小陈这家伙鬼精哩,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不少经验哩!”
老强说:“你们租在我家里,我就把你们当自家人,不希望看到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出事。靠手艺凭力气吃饭,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你们人在外面,家中父母心挂着呢,要让他们放心,多多赚钱,把日子越过越好。”
大家点头称是。张来福对老强更多了一份敬意。
散席后张来福没有回去,和沈喜宝睡在一起。
这家伙屋里收拾得还挺清爽,买了个煤油炉子,小桌上堆着筒面。
张来福问他,怎么小四子接到公章还要拿给小陈刻,沈喜宝说小陈刻公章是一绝,小四子刻不出那种笔锋来,只好给小陈刻,刻的钱两人对半分。
“看来学手艺就是要专要精,就像我原来的赵师傅,人虽然抠门,但木匠手艺确实好,方圆十里砌房造屋打家具的人家还要首先想到他!”
张来福说对的。告诉沈喜宝自己写过一封信回去了,问他有没有写。
“我还没写,”沈喜宝说,“你不怕你爸妈按照地址摸过来呀?”
“我信封上没有留地址,就是怕他们摸过来。”张来福说,“但不写不好,怕他们太担心了。”
“你怎么写的?”
“我告诉他们我在工厂上班了,一切都适应,工资也挺高,要他们放心。写得很短,但意思都到了。”
“有没有提到我?”
“倒没有。我忘提了。”
“不要紧,我如果下周能满师,我就回去一趟。我学成了手艺,能够自己挣钱了,谅他们也不会不高兴。”
“那你回去到我家去一趟,我暂时是不会回去的,回去了就出不来了!”
“好的。”
“腊梅怎么办?你带她过来吗?”
“其实我天天都想到腊梅,你看我这身上,穿着她哥哥的衣服呢!”沈喜宝担忧地叹了口气,“就怕凭我现在这身份,去她家找她,会被她家人骂出来。”
“你想想办法么,我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她的。她肯定天天在家里等我们信呢!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失了信,弄得她走投无路出了事,我俩就是罪人一对!”张来福声音大了起来。
沈喜宝听得额头上都沁汗了,连连说:“好,我想办法!”
张来福沉吟了一会儿,说:“我觉得腊梅的事还得请老强帮忙,他肯帮人,也肯定有路子。”
“对对,那我明天就跟他讲!”沈喜宝听了,脸上愁云顿时消掉一半,立即同意。
“你要婉转地对老强讲,注意措辞,别急急呛呛的。”
“好的,好的!”
下午下班后就急忙洗澡换衣,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出了农药厂大门。
他要去看沈喜宝,了解他这一周的情况。
不到下午六点,太阳还悬在西天,估计沈喜宝和他的师傅小四子还没收摊,便径直朝南门街而去。
他听小四子说的,刻章的早市、晚市是不能丢的,也就是说,要起早带晚,上班和下班时间街上人流涌涌的,生意概率比较大。
到了那儿,果然两人还在。
小四子正在给一个拎着买菜布兜的老妇人刻章,沈喜宝聚精会神地凑在一边看。
小四子的刻字摊非常简单,就是在香烟纸箱上蒙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几十个各种规格的章料子,一个印油盒和一本收据。
他是无照无证刻章,自然没有发票,要发票只能给收据;另外收据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刻好章后在上面盖给人家看,满意给钱。
摊子前沿倚着一块杂志大的三夹板,上面写着“快速刻字”。
小四子刻私章不用先在章料上写反字,也不用固定夹,直接捏在手上刻,他用的是自制的钢锯条磨成的刻刀,用胶布缠着刀柄,柔中带刚,先打边框,分字格,然后直接刻字。
他刀法十分娴熟,刀尖“噼啪”有声,很快就刻好了,蘸上印油,使劲往收据上一盖,殷红的印章赫然在目。
那妇女点点头,掏出四块钱给他,笑眯眯地走了。
小四子吁了一口气,掏出香烟来,自己叼一根,递一根给沈喜宝,两人凑着脑袋点上,一副师徒乐的样子。
旁过头来,才看见张来福站在一边。
“来福,你怎么来了?”沈喜宝喜悦地叫道。
“对对,今天是周末,我倒忘了!”小四子笑道,赶紧招呼张来福坐下——他用报纸包着两块砖头,供顾客歇脚的;沈喜宝也是坐的这样的“凳”。
张来福接过小四子递过的烟刚点上,沈喜宝便迫不及待地问起他在农药厂的情况来。
“怎么样,苦不苦,还能适应吗?”
“谈不上苦,有力气就行。有什么不能适应的,能适应。”张来福轻描淡写地说,“反正进厂也是过渡,挣够做生意的本钱就出来了。”
反过来问他:“你呢,刻章学得怎么样了?”
“我师傅说我进步快,有悟性哩!”沈喜宝嘻嘻笑,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章料子来,摆在摊子角上,有七八枚之多。
张来福拿来看,原来上面都刻上了字。大多是独体字,如“王”、“玉”、“正”“田”、“日”等;也有简单的合体字,如“明”“林”“杜”、“宝”、“直”等。
虽然笔划粗细不均,还有断裂的,但总体上横平竖直,像小学生认真写下的铅笔字。
“不错,不错!”张来福称赞。
“先从简单的字刻,刻熟了再刻复杂的。”小四子笑着告诉他。
“这些章料子怎么不齐整?”张来福问。
他发现沈喜宝给他看的这些图章长短不均,有的只有本来的一半长短。
“这是磨短的。”沈喜宝抢着解释,“我师傅要我刻了磨,磨了刻,把章料子磨得捏不上手了,基本功也就差不多了。”
“我懂了,同时这也节约实习材料!”张来福嘴里说着,心里却在想:沈喜宝这家伙,二十四岁的高考落榜生,对十八岁的初一都没念完的小四子一口一个“我师傅”,听起来怎么有些别扭呀?可能自己潜意识中还是有些瞧不起小四子。
这是不应该的,小四子对他们多接纳、多热心、多真诚!
不能因为小四子家庭背景比自己差、读书不如自己多和比自己岁数小就产生轻视之心;另外这个时候恃才自傲是可笑的,人家通过做手艺一天能挣几十块钱,你呢?你才是个刚刚上班的临时工!
还有,沈喜宝不称小四子师傅称什么,两人现在本来就是师徒关系——如果现在再喊他“小四子”,那就不上规矩不懂礼貌了。
他对沈喜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你下了大功夫,难怪进步这么快。”
小四子说:“再过一个礼拜,我估计就喜宝就可以出师了。”
张来福笑道:“他学木匠两年,师傅都没教他真功夫,现在跟你学刻章,半个月就能出师了——师傅跟师傅就是不一样啊!”
沈喜宝也跟着讪讪地笑:“是的,不一样。”
“这是应该的么,承蒙你们看得起我,到扬州来投奔我,我也自豪哩!把你们俩安排出来,以后我到了庄上说起来脸上有光哩!”小四子说着,离开小板凳站了起来,指示沈喜宝:“收摊吧,咱们买菜去!”
沈喜宝问:“师傅,不再等个把生意?”
“不等了,来福来了,早点回去弄饭,喝酒!”
晚上照例如同上次一样,借了房东老强家的客厅吃饭,把房客们全部请到。
事后小四子讲,出门在外讨生活,最讲究跟房东房客处好关系,买来的菜三个人也是吃,大家一起也是吃,多几双筷子而已,却多了热闹和亲热;朋友之间是吃来吃去的,今天你喊他,明天他也会喊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是个宝,关键时候少不了。
听了小四子这些靠谱的江湖话,张来福心里感到佩服,好多知识和经验是学校里课本上学不到的,必须亲身体验才能懂得和掌握。
席间老强问了张来福工作情况,张来福一一作了回答,说自己能够胜任,让老强放心。
小陈一喝酒话就多,爱显摆,问大家小白今天晚上穿的这件连衣裙好看不好看。
这小白是泰州苏陈的,跟小陈老乡,在一家茶社上班,只做一顿早市,下午便没事了,不是到老西门小陈摊点上陪着,就是回家钻进楼梯间睡觉,小陈经常笑骂她是个“懒丫头”,人长得像个又白又暄的肉包子。
其实小白是胖得瓷实,胖得健康,简直胖得理所当然,不胖倒不是小白了。
这姑娘喜眉笑眼,没有心机,随你怎么跟她开玩笑都不生气,农村人常说没心没肺的人是“福人”,因为不生气人缘就好,不生气人就不生病,人缘好就四邻和睦,不生病就长命百岁。
张来福的审美层次高,他觉得这样的姑娘也挺好,他喜欢笑眉笑眼一团和气的人。
今晚小白穿了一件簇新的白衣连衣裙,就像一朵盛开的白牡丹,大家都说好看。
听大家都赞扬,小陈乐不可支,告诉大家下午刻了个公章,对方没有介绍信,宰了人家五十块钱,被小白知道了,硬把钱要过去买了条裙子。
“自从跟她谈恋爱,我就落不下几个钱来,又要吃零食又要供衣服——这个败家婆娘!”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老强却正色道:“小陈,我知道你手艺好,但公章这东西我劝你还是不要碰,万一出了事是要坐牢的,到时候恐怕我这个房东都要受牵连!”
小陈说他很小心的,基本都是刻有介绍信的公章,没有介绍信看抬头,抬头太“大”坚决不刻。
他指着小四子说:“上次小四子接了个公章,抬头是公安局,送给我刻,被我骂了一顿——就是给一千块钱也不能刻呀——公安局的章还要找我们野摊子刻么?还没有介绍信!来刻章的分明是个犯罪分子么!”
小四子笑着对大家说:“小陈这家伙鬼精哩,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不少经验哩!”
老强说:“你们租在我家里,我就把你们当自家人,不希望看到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出事。靠手艺凭力气吃饭,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你们人在外面,家中父母心挂着呢,要让他们放心,多多赚钱,把日子越过越好。”
大家点头称是。张来福对老强更多了一份敬意。
散席后张来福没有回去,和沈喜宝睡在一起。
这家伙屋里收拾得还挺清爽,买了个煤油炉子,小桌上堆着筒面。
张来福问他,怎么小四子接到公章还要拿给小陈刻,沈喜宝说小陈刻公章是一绝,小四子刻不出那种笔锋来,只好给小陈刻,刻的钱两人对半分。
“看来学手艺就是要专要精,就像我原来的赵师傅,人虽然抠门,但木匠手艺确实好,方圆十里砌房造屋打家具的人家还要首先想到他!”
张来福说对的。告诉沈喜宝自己写过一封信回去了,问他有没有写。
“我还没写,”沈喜宝说,“你不怕你爸妈按照地址摸过来呀?”
“我信封上没有留地址,就是怕他们摸过来。”张来福说,“但不写不好,怕他们太担心了。”
“你怎么写的?”
“我告诉他们我在工厂上班了,一切都适应,工资也挺高,要他们放心。写得很短,但意思都到了。”
“有没有提到我?”
“倒没有。我忘提了。”
“不要紧,我如果下周能满师,我就回去一趟。我学成了手艺,能够自己挣钱了,谅他们也不会不高兴。”
“那你回去到我家去一趟,我暂时是不会回去的,回去了就出不来了!”
“好的。”
“腊梅怎么办?你带她过来吗?”
“其实我天天都想到腊梅,你看我这身上,穿着她哥哥的衣服呢!”沈喜宝担忧地叹了口气,“就怕凭我现在这身份,去她家找她,会被她家人骂出来。”
“你想想办法么,我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她的。她肯定天天在家里等我们信呢!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失了信,弄得她走投无路出了事,我俩就是罪人一对!”张来福声音大了起来。
沈喜宝听得额头上都沁汗了,连连说:“好,我想办法!”
张来福沉吟了一会儿,说:“我觉得腊梅的事还得请老强帮忙,他肯帮人,也肯定有路子。”
“对对,那我明天就跟他讲!”沈喜宝听了,脸上愁云顿时消掉一半,立即同意。
“你要婉转地对老强讲,注意措辞,别急急呛呛的。”
“好的,好的!”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