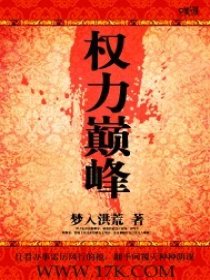正文:第1章 有凤来仪
1977年正月十五,栗园庄村下了一夜漫天的大雪,天麻麻亮的时候,李天印听到院子里“咔嚓”一声响,打了个激灵,醒了,披被坐起,猛然间发现床那头老婆旁边的被窝塌着,心里骂了句,这么早就出去了,这死冷的天,这孩子天生就是个劳碌命,从不睡懒觉,天天起的比家养的鸡都早。外面正雪还在下着,想到刚才那声巨响,李天印心中咯噔了一下,坏了,不会是这小丫头片子出啥事了?
李天印摇了摇老婆王菊香,她翻了个身,将大半个白生生的后背晾了出来,李天印替她盖好被子,心里涌出一股怜惜,叹息一声,孩子多,可苦了这婆娘了,天天脚下象蹬了风火轮似的,走路都能被绊倒。
李天印心里琢磨着,蹑手蹑脚打开房门,生怕弄出些响动打搅了孩子们的好梦。
大女儿走亲戚没回来,四个儿子都还没起床。下雪天,反正也干不成啥活,家里也没有炭火可以取暖,就让他们享受这难得的悠闲吧。
好大的雪啊,院子里盖上了层厚厚的积雪,大雪将本是杂乱无章的院子变的笔画简单又粗劣。
李天印环视了一下院子,两排一间间格开的小屋全是黑的,只听见簌簌落雪的声音。
耀眼的雪光刺激地他用袖子捂了下眼睛,几秒钟后他才适应了光线。
一个冬天都是干冷的,没想到却在年后下了这场雪。
早该下了,地里的庄稼都快要干死了。这年头,庄稼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这是一座专门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盖的知青院。在栗园庄村算得上最好的房子,共有三十多个小间。每间房子都安有木门,门上刷有红色的油漆。房子有些年头了,门框和窗框上的油漆都有些脱落,露出些木头的原样来。
知青院以前也热闹的很,住满了男男女女下乡的青年,多是些京城里的孩子。近几年随着知青回城政策的陆续出台,符合政策的陆续回了城,只剩下三三两两的知青还住在这里,随时等待回城的消息。
李天印家原来住在村后面西沟沟脑的半坡上,独门独户。祖辈几代人倒也安居乐业,与世无争。谁想到,一场下了近两个月的连阴雨,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塌了。
李天印十分愧疚,祖上留下来的唯一的家产就这样败落在自己手中。
房塌了,等于家没了,看着一大家子人在阴雨中瑟瑟的样子,李天印只好去找生产队解决问题。
队长王安邦比他小五岁,小时候也是经常在一起玩耍。
王安邦和崔会计商量了下,让他们搬到知青院闲置的空房子居住,顺便让王菊香照顾三个知青的饮食起居。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不方便住在知青院,就让他们一家暂住在生产队的饲养室。
栗园庄村隶属怀山县栗树区栗树公社,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自古以来就是圣贤倍出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怀山是燕国战略要地,栗园庄村就是渔阳郡首府。栗园庄村以盛产板栗而闻名天下。村民以王姓为大姓,夹杂些其他姓氏。民风淳朴,风景如画,是个适合人居住的好地方。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但生活似乎和以前又有了新的不同。搬到知青院,解决了以前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屋子的局面,另一种危机却也接踵而来。
李天印夫妻渐渐开始不安起来。住在知青院,年龄不相上下的清林、清霞两兄妹和三个城里青年出入成双,打成一片,在落后闭塞的栗园庄村难免显得有些刺目。
按理来说,年青人在一起打打闹闹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是身份不同的人。
这些城里的孩子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他们迟早是要回城的,自己的孩子却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这是一种本质上的区别,容不得出任何差池。
村里不时有闲言传来,这让李天印和王菊香夫妻俩喜忧参半,时不时敲打一双儿女,要他们和知青保持适当距离。
夜深人静的时候,两口子就发愁。
大女儿二十出头,早到了找婆家的年龄。每次和她提起,她都说不急。时间长了,他们也懒得唠叨。孩子大了不由娘,王菊香知道她心气高,想找个自己中意的人过日子。每天除了到地里上工,各种家务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去关心她的个人问题。他们希望儿女们该娶的娶,该嫁的嫁,到啥时候说啥话。可事实却是,哪户人家愿意和他们结这门穷亲?
眼看二儿子都奔三了还是光棍一条,李天印夫妻由刚开始的无所谓很快发展成焦虑不安。他们甚至也产生过用大女儿换亲的想法。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使不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即使让儿子打光棍,他们也不会把女儿当成商品去交换。
好女不愁嫁,更何况清霞模样俊俏,又识文断字,只要她愿意,找个婆家根本不费事。可就是清林这犊子让两口子日夜不安。清林眼头高,长相一般的姑娘看不上,总说要找个要才貌双全体贴贤惠的,宁缺勿滥。
一双儿女到了结婚年龄却不婚娶,两口子在村里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每次想起这事李天印就长吁短叹。
李天印瞅了瞅被大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院墙,将两只手笼在袖筒中,微佝着背。他一米七八的个头,年青的时候腰板挺的象根电线杆,到了五十多岁就被生活压的早早驼了背。
李天印吃惊的发现,位于大门旁边那棵本来就令他看着不顺眼逾百年的老柿子树一枝横生的树杆被雪压断了,刚刚惊醒他的声音正是来自于它。
这棵树在他记事的时候就活着,村子里盖知青院的时候有人建议将它砍了,又有年长的人说树年头多了有了灵性,动不得的。它才得以存活下来,竟然成为院子里唯一的景观。
李天印无暇顾及雪地里散落了一地的树枝,“华华,华华”焦急地呼唤着女儿的小名。
一颗小脑袋从柿树后面冒出来,手中握了一团雪白,调皮地冲他做了个鬼脸,嘻笑着说:“爸爸,我在这。”
李天印脸上立即多云转睛,皱纹迅速聚集到一起,笑着骂了句:“臭丫头,这冷的天,热被窝不躺,起这早干啥?看你,身上都淋湿了。”
李天印快走几步到女儿跟前,拍了拍落在她身上的雪,拉了她就要进屋。
小女孩挣脱他的手说:“爸,我不回去,我要把雪景画下来。”
她大眼睛,双眼皮,皮肤雪白,头发扎成了两把小刷子,小脸蛋冻的通红,小巧的嘴角透出一丝倔强。
农村有句方言,偏大的爱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李天印不承认,他总说自己对儿女一个样,可七个手指头还不一样长,能够会有亲疏之分。中年得女,小女儿就是李天印含在嘴里的一颗棉花糖。
在有了小女儿之前,李天印已经生了七个孩子。
五个儿子都泛一个“清”字,依次叫清华清林清河清朋清元,大女儿排行第四,起名清霞。小女儿排行第六,刚生下来就被过继给王菊香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再去问,只说没养成,李天印两口子也不去考证,反正已经是别的人了,无所谓了。只是,每次想起,心里还是不舒服。
正月初六李清霞就离开了家,说是要去北京城一远房亲戚家串门。两口子拦也拦不住,女孩子大了,有了心思,他们也希望她能多出去走走,一来可以见见世面,二来指不定还能遇个好人家。
小女儿出生的时候,李天印在起名字这件事上颇费了一番功夫,将家中刚攒的十多颗鸡蛋包了,请王安邦取名。李天印和王安邦从小一起玩到大,算是他这辈子结识最大的官。
在栗园庄村,王安邦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既是一队之长又是最有文化的人,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是主事管账的先生。
王安邦瞅了瞅鸡蛋,又看了眼孩子,煞有介事的问王菊香怀孩子时有没有做过好梦。王菊香想了好半天,说总是梦到一棵又高又大的栗子枝,开满了栗子花。王安邦掐着指头说:“这是个好梦,树是开枝散叶的意思,你家这丫头将来肯定有出息,叫怡华好了,怡是好的意思,华也是好的意思,两好加一好将来必成大器。”
王安邦说的唾沫横飞,李天印两口子听的心花怒放。
农村人不懂得采取节育措施,李天印夫妻每隔几年家中就会添丁进口。等到了奔五的年纪,实实是生孩子生怕了,谁想到又怀了这一胎。心里想着,反正一个也是养,一窝也是养,来就来吧,都是命中的缘分。
老大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到生产队挣工分,后来成了家分家另过。老二和大女儿中学毕业回村当了社员。老三是所有儿女中最有出息的,考了京城的师范学院正在上学。老四老五中间各差了几岁。
农闲的时候,村民们在一起扯闲话,就会笑李天印的种子好王菊香的地好,说他们的娃娃生了足足一个排。李天印有苦难言,他也不想那样,七八张嘴天天都要吃饭,队上分的粮食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一个字,穷啊。
李天印夫妻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半辈子,自认为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到了儿女这一辈,他们卯足了劲供他们上学,能上到啥程度是啥程度。偏这老四儿子是个最不争气的,书念不进去,早早主动要求辍学回家。李天印两口子拿他也没办法,只好顺了他的意。却好吃懒做,也挣不了几个工分。
人常说三岁看大,小女儿李怡华带给他们的除了天伦之乐,还有更大的惊喜,就是聪慧。三岁时的李怡华用小石头在大石头上画的东西都已经惟妙惟肖了。七岁时王菊香为了能多挣些工分,硬是要把她送到村小学让她上学。在栗园庄村,孩子们都是十岁才入学。学校嫌她年龄太小不收,王菊香拿着李怡华的画找到校长,校长直呼“孺子可教也。”破例让李怡华提前入学。
李天印见小女儿不愿回屋,寻思着不如考考她。
李天印瞅了瞅院门楼上“知青院”三个大字,笑着问道:“华华,这三个字读啥?你要是认不得就必须回家。”
李怡华咧开嘴笑了笑,说:“爸,我才没那么笨,我都上二年级了,这么简单的字能不认识?这座院子是专门给盈盈姐他们这些城里知青盖的,叫知青院。”
李天印摇了摇老婆王菊香,她翻了个身,将大半个白生生的后背晾了出来,李天印替她盖好被子,心里涌出一股怜惜,叹息一声,孩子多,可苦了这婆娘了,天天脚下象蹬了风火轮似的,走路都能被绊倒。
李天印心里琢磨着,蹑手蹑脚打开房门,生怕弄出些响动打搅了孩子们的好梦。
大女儿走亲戚没回来,四个儿子都还没起床。下雪天,反正也干不成啥活,家里也没有炭火可以取暖,就让他们享受这难得的悠闲吧。
好大的雪啊,院子里盖上了层厚厚的积雪,大雪将本是杂乱无章的院子变的笔画简单又粗劣。
李天印环视了一下院子,两排一间间格开的小屋全是黑的,只听见簌簌落雪的声音。
耀眼的雪光刺激地他用袖子捂了下眼睛,几秒钟后他才适应了光线。
一个冬天都是干冷的,没想到却在年后下了这场雪。
早该下了,地里的庄稼都快要干死了。这年头,庄稼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这是一座专门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盖的知青院。在栗园庄村算得上最好的房子,共有三十多个小间。每间房子都安有木门,门上刷有红色的油漆。房子有些年头了,门框和窗框上的油漆都有些脱落,露出些木头的原样来。
知青院以前也热闹的很,住满了男男女女下乡的青年,多是些京城里的孩子。近几年随着知青回城政策的陆续出台,符合政策的陆续回了城,只剩下三三两两的知青还住在这里,随时等待回城的消息。
李天印家原来住在村后面西沟沟脑的半坡上,独门独户。祖辈几代人倒也安居乐业,与世无争。谁想到,一场下了近两个月的连阴雨,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塌了。
李天印十分愧疚,祖上留下来的唯一的家产就这样败落在自己手中。
房塌了,等于家没了,看着一大家子人在阴雨中瑟瑟的样子,李天印只好去找生产队解决问题。
队长王安邦比他小五岁,小时候也是经常在一起玩耍。
王安邦和崔会计商量了下,让他们搬到知青院闲置的空房子居住,顺便让王菊香照顾三个知青的饮食起居。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不方便住在知青院,就让他们一家暂住在生产队的饲养室。
栗园庄村隶属怀山县栗树区栗树公社,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自古以来就是圣贤倍出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怀山是燕国战略要地,栗园庄村就是渔阳郡首府。栗园庄村以盛产板栗而闻名天下。村民以王姓为大姓,夹杂些其他姓氏。民风淳朴,风景如画,是个适合人居住的好地方。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但生活似乎和以前又有了新的不同。搬到知青院,解决了以前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屋子的局面,另一种危机却也接踵而来。
李天印夫妻渐渐开始不安起来。住在知青院,年龄不相上下的清林、清霞两兄妹和三个城里青年出入成双,打成一片,在落后闭塞的栗园庄村难免显得有些刺目。
按理来说,年青人在一起打打闹闹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是身份不同的人。
这些城里的孩子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他们迟早是要回城的,自己的孩子却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这是一种本质上的区别,容不得出任何差池。
村里不时有闲言传来,这让李天印和王菊香夫妻俩喜忧参半,时不时敲打一双儿女,要他们和知青保持适当距离。
夜深人静的时候,两口子就发愁。
大女儿二十出头,早到了找婆家的年龄。每次和她提起,她都说不急。时间长了,他们也懒得唠叨。孩子大了不由娘,王菊香知道她心气高,想找个自己中意的人过日子。每天除了到地里上工,各种家务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去关心她的个人问题。他们希望儿女们该娶的娶,该嫁的嫁,到啥时候说啥话。可事实却是,哪户人家愿意和他们结这门穷亲?
眼看二儿子都奔三了还是光棍一条,李天印夫妻由刚开始的无所谓很快发展成焦虑不安。他们甚至也产生过用大女儿换亲的想法。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使不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即使让儿子打光棍,他们也不会把女儿当成商品去交换。
好女不愁嫁,更何况清霞模样俊俏,又识文断字,只要她愿意,找个婆家根本不费事。可就是清林这犊子让两口子日夜不安。清林眼头高,长相一般的姑娘看不上,总说要找个要才貌双全体贴贤惠的,宁缺勿滥。
一双儿女到了结婚年龄却不婚娶,两口子在村里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每次想起这事李天印就长吁短叹。
李天印瞅了瞅被大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院墙,将两只手笼在袖筒中,微佝着背。他一米七八的个头,年青的时候腰板挺的象根电线杆,到了五十多岁就被生活压的早早驼了背。
李天印吃惊的发现,位于大门旁边那棵本来就令他看着不顺眼逾百年的老柿子树一枝横生的树杆被雪压断了,刚刚惊醒他的声音正是来自于它。
这棵树在他记事的时候就活着,村子里盖知青院的时候有人建议将它砍了,又有年长的人说树年头多了有了灵性,动不得的。它才得以存活下来,竟然成为院子里唯一的景观。
李天印无暇顾及雪地里散落了一地的树枝,“华华,华华”焦急地呼唤着女儿的小名。
一颗小脑袋从柿树后面冒出来,手中握了一团雪白,调皮地冲他做了个鬼脸,嘻笑着说:“爸爸,我在这。”
李天印脸上立即多云转睛,皱纹迅速聚集到一起,笑着骂了句:“臭丫头,这冷的天,热被窝不躺,起这早干啥?看你,身上都淋湿了。”
李天印快走几步到女儿跟前,拍了拍落在她身上的雪,拉了她就要进屋。
小女孩挣脱他的手说:“爸,我不回去,我要把雪景画下来。”
她大眼睛,双眼皮,皮肤雪白,头发扎成了两把小刷子,小脸蛋冻的通红,小巧的嘴角透出一丝倔强。
农村有句方言,偏大的爱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李天印不承认,他总说自己对儿女一个样,可七个手指头还不一样长,能够会有亲疏之分。中年得女,小女儿就是李天印含在嘴里的一颗棉花糖。
在有了小女儿之前,李天印已经生了七个孩子。
五个儿子都泛一个“清”字,依次叫清华清林清河清朋清元,大女儿排行第四,起名清霞。小女儿排行第六,刚生下来就被过继给王菊香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再去问,只说没养成,李天印两口子也不去考证,反正已经是别的人了,无所谓了。只是,每次想起,心里还是不舒服。
正月初六李清霞就离开了家,说是要去北京城一远房亲戚家串门。两口子拦也拦不住,女孩子大了,有了心思,他们也希望她能多出去走走,一来可以见见世面,二来指不定还能遇个好人家。
小女儿出生的时候,李天印在起名字这件事上颇费了一番功夫,将家中刚攒的十多颗鸡蛋包了,请王安邦取名。李天印和王安邦从小一起玩到大,算是他这辈子结识最大的官。
在栗园庄村,王安邦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既是一队之长又是最有文化的人,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是主事管账的先生。
王安邦瞅了瞅鸡蛋,又看了眼孩子,煞有介事的问王菊香怀孩子时有没有做过好梦。王菊香想了好半天,说总是梦到一棵又高又大的栗子枝,开满了栗子花。王安邦掐着指头说:“这是个好梦,树是开枝散叶的意思,你家这丫头将来肯定有出息,叫怡华好了,怡是好的意思,华也是好的意思,两好加一好将来必成大器。”
王安邦说的唾沫横飞,李天印两口子听的心花怒放。
农村人不懂得采取节育措施,李天印夫妻每隔几年家中就会添丁进口。等到了奔五的年纪,实实是生孩子生怕了,谁想到又怀了这一胎。心里想着,反正一个也是养,一窝也是养,来就来吧,都是命中的缘分。
老大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到生产队挣工分,后来成了家分家另过。老二和大女儿中学毕业回村当了社员。老三是所有儿女中最有出息的,考了京城的师范学院正在上学。老四老五中间各差了几岁。
农闲的时候,村民们在一起扯闲话,就会笑李天印的种子好王菊香的地好,说他们的娃娃生了足足一个排。李天印有苦难言,他也不想那样,七八张嘴天天都要吃饭,队上分的粮食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一个字,穷啊。
李天印夫妻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半辈子,自认为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到了儿女这一辈,他们卯足了劲供他们上学,能上到啥程度是啥程度。偏这老四儿子是个最不争气的,书念不进去,早早主动要求辍学回家。李天印两口子拿他也没办法,只好顺了他的意。却好吃懒做,也挣不了几个工分。
人常说三岁看大,小女儿李怡华带给他们的除了天伦之乐,还有更大的惊喜,就是聪慧。三岁时的李怡华用小石头在大石头上画的东西都已经惟妙惟肖了。七岁时王菊香为了能多挣些工分,硬是要把她送到村小学让她上学。在栗园庄村,孩子们都是十岁才入学。学校嫌她年龄太小不收,王菊香拿着李怡华的画找到校长,校长直呼“孺子可教也。”破例让李怡华提前入学。
李天印见小女儿不愿回屋,寻思着不如考考她。
李天印瞅了瞅院门楼上“知青院”三个大字,笑着问道:“华华,这三个字读啥?你要是认不得就必须回家。”
李怡华咧开嘴笑了笑,说:“爸,我才没那么笨,我都上二年级了,这么简单的字能不认识?这座院子是专门给盈盈姐他们这些城里知青盖的,叫知青院。”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