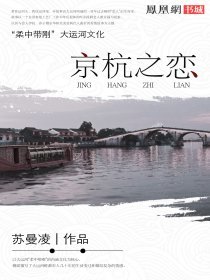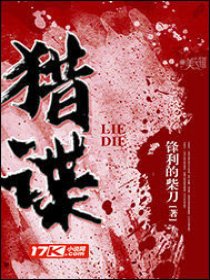第五章 青出于蓝3
一次见到兰姨,说起识字学文化的事,谢京福满口答应,却抽不出一点儿时间来,急得兰姨有些头疼,也亲自到谢家找谢慎说了好几次,但是每当谢慎看到儿子那辛苦疲惫的睡容,便有些于心不忍,于是这事就又给搁下了。
谢京福有一次被曹慧珍拦住,让他支持三姨的工作,但是谢京福与伊杭约好了,再跑一趟伊杭的族亲那里,那里似乎有文王鼎的画册,便拒绝了曹慧珍,径直跑掉了。曹慧珍看到谢京福着急的样子,觉得有些奇怪,但是还是想到他的不易,便很快释然了。
谢京福与伊杭约好,在上次后海那个酒家旁边的石头旁边见面。他拉了两个客人,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果然看到伊杭拿着一幅画册兴奋地走了过来。
“谢大哥,真是赶巧,在我族叔家里找到了这幅画册,果然和我当年画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说照着这个样子做不会错,至于尺寸,我会按照我的画按比例还原回去。这文王鼎是我们满族最喜欢的器具,有鼎有盖,上边有缠枝花卉和凤鸟纹,盖钮上还有狮子,鼎身上有饕餮纹、夔龙纹,甚是贵气雅致,《红楼梦》里可是专门有过说法,难怪有些身份的人都这样喜欢!”
谢京福听了觉得有些惭愧,他并不知道这个《红楼梦》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听过这个什么文王鼎,尤其是伊杭那天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什么意思,此刻,他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闲暇时候不好好认些字。
善解人意的伊杭早就猜到了谢京福的窘迫在哪里,她笑着说:“谢大哥,你不要愁,我早已经把这几个字样写好了,给你,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不过,听说冯先生还有一个月就要出国了,这个活计可是要加紧了,不然就怕赶不上了。”
谢京福点头,决定近些日子少拉些客人,专注来做这两个器件,不能掉链子。
“谢谢你。”
“谢大哥,还和我客气,要说谢,我可是要谢你们说上一箩筐了,这不算什么。”
谢京福看到伊杭笑得灿烂如花,一笑就露出了那珍珠贝一般的玉齿,心头渐渐醉了。这个时节的荷花虽然凋落了很多,但是荷叶还是绿的,偶尔还能在叶片下边窥到一朵金莲。微风阵阵,仿佛将那潜藏在水底的藕香翻了过来,令人充满了对丰收的憧憬。
他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激情地过日子,除了照顾好父亲的日常起居,便是没日没夜的做珐琅。很快,这两件精美的器具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而且做工精美,也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伊杭看到它们居然真的可以提前完成,十分高兴,让谢京福把他送到丝绸总店去。
而与谢京福一样充满了期待的是冯友源,与其说是他也期待着这两件精美的珐琅器的到来,不如说他想见伊杭的心超越了对所有事物的兴趣。
但是,当他仔细看到那两件流光溢彩的珐琅器之后,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恐怕自己看错了,又仔细查验了一次,才终于确定自己的眼没有看错,那些器具都在不起眼的地方刻下了“谢氏”的字眼,而最显眼的“老骥伏枥”四个字的“骥”右边的“冀”字却少了一“横”,而“枥”的最右边恰恰又多了一“横”。
伊杭也在冯友源异样的眼神中看出了端倪,她仔细看了那屏风,脸色顿时大变:“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们疏忽了。”
冯友源看到伊杭那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有些不忍:“这个,应该还是有办法补救的吧?”
“您在国内还要呆多久?”
“还有大约两个礼拜时间。”
伊杭郑重点头:“我就拿回去重新做,十天内一定送回来。”
冯友源挥着手想说:“不,不要急,我可以先带一件走,下次再带另外一件……”
但是,伊杭只是深深鞠了一躬,便抱起那屏风飞快离开了。
一直在外边等待的谢京福看到伊杭失魂落魄地抱着那屏风走了过来,脸色凝重,默默地坐到车上,说:“怎么?”
“谢大哥,我们回去说。”
谢京福心头暗沉起来,一路跑着不敢吭声,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一直到了两个人常来的老地方。
“谢大哥,这个文化的事,你还是要当回事,否则,这条路很难走,我想,谢大哥不想回到谢家以往的老路上去吧?”
谢京福看到伊杭将抱着的屏风给自己看,她纤细的手指指着那几个字说:“这也怪我,应该先让你多熟悉一下这几个字再做,现在这四个字错了两个,修复的时间却只有十天,谢大哥可有把握按时完成。”
谢京福这才知道由于自己的浅薄无知犯了大错,越担心出事就越有问题,他这次是不折不扣地让伊杭丢了面子,这样想着,他的脸也发起烧来:“都是我的错,我应该仔细多看两遍,多习练两遍再做就好了。”
“事到如今,再多说也无益,只要能按时补救还来的及。不过,过了这事,谢大哥,你每隔两天就到这个地方来,我来教你认些字,这样坚持一两年,谢大哥就会觉得轻松了。”
谢京福想到街道委员会给自己家安排的“扫盲”任务还没有完成,真恨自己不早点多学文化知识,才落得今天这般耻辱。此刻恨不得将自己整个人都钻到地缝里去。他看到伊杭水波不惊的贵族气质,忽然想到了一件恐慌的事。他与她的距离,仍旧是那样遥远,也许,是从来都不曾接近过。
他呆呆地回到家里,也没有吃饭,就赶紧想办法修复它。说来容易,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每次烧蓝,都是靠着经验才能完成,温度不同,色彩也不同,怕就怕这次烧出来的颜色会和以前不同,那还不如不修。于是,他垂着头,默不出声。
谢慎看到儿子衰颓的样子,就知道他遇到的棘手的事情,心里慨叹了几声。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珐琅匠人如果没有承受能力,怕是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于是,谢慎拄着一只单拐,趁着夕阳落山时候的柔和光线,伸出右手,看着自己的手指。他心中用了无数次力,但是那大拇指和食指还是没有丝毫响应。他看着满屋子的铜器、铜丝、铜片和没有做完的珐琅瓶,儿子的脸上几乎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哀愁,不由心中哀鸿遍野。做了一辈子珐琅,到现在这珐琅事业真的要终结了。虽然有儿子可以承继家业,但是还是弥补不了他内心的失落。
他用烟袋敲着儿子的头,咳了一声,说:“犯了错算什么,改了就是,我这老头子都残废了,还没有唉声叹气,你现在这个怂样儿给谁看?听我的,去拿工具来,我给你看着,今天晚上加班把那几个字全部重新掐出来,明天去找你周文定大叔,他对烧釉最有经验了,有他指点,准成了。”
谢京福听了这几句话,终于有了些精神,他点了点头,按照父亲的吩咐做了起来。深夜秋风习习,庭院里月色撩人,谢京福静下心来,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夜。他终于成功地做好了那些工艺,不放心又对照了几遍,确信无疑才起身。
谢京福心里还是最佩服老一辈的珐琅匠,在周叔的指导下,这屏风居然只花了七天时间就修复如初,丝毫看不出有改过的痕迹。他将屏风交到伊杭手中的时候,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
他有些不敢面对伊杭,但是伊杭仿佛并不在意,而是定期拿着写好的字,教谢京福认,还让他回去照着笔画多练习几遍。
这段日子,谢京福过得忐忑而开心,他很珍惜这难得的相处,也渐渐想开了。如果不是这样的缘由,他怎么有机会多见几回伊杭的面呢?她家里那个门第,是个超越于现实的所在,既近又远,难以想象以后的日子。
谢慎在自己家的庭院里,忽然看到了曹慧珍,只见她先到谢京福的屋子里整理了一番,又拿起一把大扫帚,正在清理地上的枯叶杂物。他年纪大了却不愚钝,看的出自己的儿子并不喜欢这姑娘。但是,这姑娘明明在天津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却甘愿放弃,来自己家奉献,这样的品性也是难寻。
几只大雁在高空划过,很快变成了几个黑点,直到渐渐消失。那婆娑的扫地声,也似乎有了些哀怨的气息,而儿子还没有回来。谢慎想,这辈子他已经亏欠了兰姨很多,这一次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覆辙了。日子是过出来的,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培养出感情来的。他打定主意,决定要赶紧把儿子的婚事定下来。
谢京福有一次被曹慧珍拦住,让他支持三姨的工作,但是谢京福与伊杭约好了,再跑一趟伊杭的族亲那里,那里似乎有文王鼎的画册,便拒绝了曹慧珍,径直跑掉了。曹慧珍看到谢京福着急的样子,觉得有些奇怪,但是还是想到他的不易,便很快释然了。
谢京福与伊杭约好,在上次后海那个酒家旁边的石头旁边见面。他拉了两个客人,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果然看到伊杭拿着一幅画册兴奋地走了过来。
“谢大哥,真是赶巧,在我族叔家里找到了这幅画册,果然和我当年画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说照着这个样子做不会错,至于尺寸,我会按照我的画按比例还原回去。这文王鼎是我们满族最喜欢的器具,有鼎有盖,上边有缠枝花卉和凤鸟纹,盖钮上还有狮子,鼎身上有饕餮纹、夔龙纹,甚是贵气雅致,《红楼梦》里可是专门有过说法,难怪有些身份的人都这样喜欢!”
谢京福听了觉得有些惭愧,他并不知道这个《红楼梦》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听过这个什么文王鼎,尤其是伊杭那天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什么意思,此刻,他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闲暇时候不好好认些字。
善解人意的伊杭早就猜到了谢京福的窘迫在哪里,她笑着说:“谢大哥,你不要愁,我早已经把这几个字样写好了,给你,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不过,听说冯先生还有一个月就要出国了,这个活计可是要加紧了,不然就怕赶不上了。”
谢京福点头,决定近些日子少拉些客人,专注来做这两个器件,不能掉链子。
“谢谢你。”
“谢大哥,还和我客气,要说谢,我可是要谢你们说上一箩筐了,这不算什么。”
谢京福看到伊杭笑得灿烂如花,一笑就露出了那珍珠贝一般的玉齿,心头渐渐醉了。这个时节的荷花虽然凋落了很多,但是荷叶还是绿的,偶尔还能在叶片下边窥到一朵金莲。微风阵阵,仿佛将那潜藏在水底的藕香翻了过来,令人充满了对丰收的憧憬。
他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激情地过日子,除了照顾好父亲的日常起居,便是没日没夜的做珐琅。很快,这两件精美的器具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而且做工精美,也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伊杭看到它们居然真的可以提前完成,十分高兴,让谢京福把他送到丝绸总店去。
而与谢京福一样充满了期待的是冯友源,与其说是他也期待着这两件精美的珐琅器的到来,不如说他想见伊杭的心超越了对所有事物的兴趣。
但是,当他仔细看到那两件流光溢彩的珐琅器之后,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恐怕自己看错了,又仔细查验了一次,才终于确定自己的眼没有看错,那些器具都在不起眼的地方刻下了“谢氏”的字眼,而最显眼的“老骥伏枥”四个字的“骥”右边的“冀”字却少了一“横”,而“枥”的最右边恰恰又多了一“横”。
伊杭也在冯友源异样的眼神中看出了端倪,她仔细看了那屏风,脸色顿时大变:“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们疏忽了。”
冯友源看到伊杭那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有些不忍:“这个,应该还是有办法补救的吧?”
“您在国内还要呆多久?”
“还有大约两个礼拜时间。”
伊杭郑重点头:“我就拿回去重新做,十天内一定送回来。”
冯友源挥着手想说:“不,不要急,我可以先带一件走,下次再带另外一件……”
但是,伊杭只是深深鞠了一躬,便抱起那屏风飞快离开了。
一直在外边等待的谢京福看到伊杭失魂落魄地抱着那屏风走了过来,脸色凝重,默默地坐到车上,说:“怎么?”
“谢大哥,我们回去说。”
谢京福心头暗沉起来,一路跑着不敢吭声,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一直到了两个人常来的老地方。
“谢大哥,这个文化的事,你还是要当回事,否则,这条路很难走,我想,谢大哥不想回到谢家以往的老路上去吧?”
谢京福看到伊杭将抱着的屏风给自己看,她纤细的手指指着那几个字说:“这也怪我,应该先让你多熟悉一下这几个字再做,现在这四个字错了两个,修复的时间却只有十天,谢大哥可有把握按时完成。”
谢京福这才知道由于自己的浅薄无知犯了大错,越担心出事就越有问题,他这次是不折不扣地让伊杭丢了面子,这样想着,他的脸也发起烧来:“都是我的错,我应该仔细多看两遍,多习练两遍再做就好了。”
“事到如今,再多说也无益,只要能按时补救还来的及。不过,过了这事,谢大哥,你每隔两天就到这个地方来,我来教你认些字,这样坚持一两年,谢大哥就会觉得轻松了。”
谢京福想到街道委员会给自己家安排的“扫盲”任务还没有完成,真恨自己不早点多学文化知识,才落得今天这般耻辱。此刻恨不得将自己整个人都钻到地缝里去。他看到伊杭水波不惊的贵族气质,忽然想到了一件恐慌的事。他与她的距离,仍旧是那样遥远,也许,是从来都不曾接近过。
他呆呆地回到家里,也没有吃饭,就赶紧想办法修复它。说来容易,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每次烧蓝,都是靠着经验才能完成,温度不同,色彩也不同,怕就怕这次烧出来的颜色会和以前不同,那还不如不修。于是,他垂着头,默不出声。
谢慎看到儿子衰颓的样子,就知道他遇到的棘手的事情,心里慨叹了几声。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珐琅匠人如果没有承受能力,怕是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于是,谢慎拄着一只单拐,趁着夕阳落山时候的柔和光线,伸出右手,看着自己的手指。他心中用了无数次力,但是那大拇指和食指还是没有丝毫响应。他看着满屋子的铜器、铜丝、铜片和没有做完的珐琅瓶,儿子的脸上几乎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哀愁,不由心中哀鸿遍野。做了一辈子珐琅,到现在这珐琅事业真的要终结了。虽然有儿子可以承继家业,但是还是弥补不了他内心的失落。
他用烟袋敲着儿子的头,咳了一声,说:“犯了错算什么,改了就是,我这老头子都残废了,还没有唉声叹气,你现在这个怂样儿给谁看?听我的,去拿工具来,我给你看着,今天晚上加班把那几个字全部重新掐出来,明天去找你周文定大叔,他对烧釉最有经验了,有他指点,准成了。”
谢京福听了这几句话,终于有了些精神,他点了点头,按照父亲的吩咐做了起来。深夜秋风习习,庭院里月色撩人,谢京福静下心来,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夜。他终于成功地做好了那些工艺,不放心又对照了几遍,确信无疑才起身。
谢京福心里还是最佩服老一辈的珐琅匠,在周叔的指导下,这屏风居然只花了七天时间就修复如初,丝毫看不出有改过的痕迹。他将屏风交到伊杭手中的时候,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
他有些不敢面对伊杭,但是伊杭仿佛并不在意,而是定期拿着写好的字,教谢京福认,还让他回去照着笔画多练习几遍。
这段日子,谢京福过得忐忑而开心,他很珍惜这难得的相处,也渐渐想开了。如果不是这样的缘由,他怎么有机会多见几回伊杭的面呢?她家里那个门第,是个超越于现实的所在,既近又远,难以想象以后的日子。
谢慎在自己家的庭院里,忽然看到了曹慧珍,只见她先到谢京福的屋子里整理了一番,又拿起一把大扫帚,正在清理地上的枯叶杂物。他年纪大了却不愚钝,看的出自己的儿子并不喜欢这姑娘。但是,这姑娘明明在天津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却甘愿放弃,来自己家奉献,这样的品性也是难寻。
几只大雁在高空划过,很快变成了几个黑点,直到渐渐消失。那婆娑的扫地声,也似乎有了些哀怨的气息,而儿子还没有回来。谢慎想,这辈子他已经亏欠了兰姨很多,这一次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覆辙了。日子是过出来的,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培养出感情来的。他打定主意,决定要赶紧把儿子的婚事定下来。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