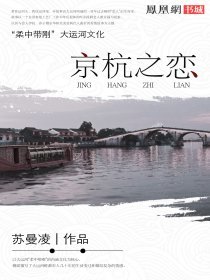第六章 柳暗花明1
秋风萧瑟,黄叶漫舞,满大街的人依旧匆匆走着。东安市场的北面,一家写着“梁记”细瓷紫砂的老店面门口,一个汉子挑着两筐刚刚下来的黄橙橙的鸭梨,沿街叫卖着。隔壁是家副食佐料铺子,招牌有些陈旧,大字依旧看得清清楚楚,上边写着“红糖、白糖、木耳、花椒、大料、五香粉、胡椒面,应有尽有”,门前有一堆人正排着队等候着铺子开门。一旁的一间房门户里,忽然门开了,里边出来个五六十岁、身材矮胖的老爷子,推着一辆独轮小车,车上是一坛子自家酿制的黄酒,朝外而来。再往里走,就是一家“福顺成衣铺”,写着专门定制旗袍。
谢京福与曹慧珍一前一后,往里边瞧着,挤过了一群又一群人。这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曹慧珍第一次来,兴奋地转着,忽然指着前边一家写着“杭州丝绸分店”的店面,笑着说:“福哥,我们去那里吧!”
谢京福无奈,只好答应。父亲让自己带着曹慧珍来买块上等的料子,这些天都是曹慧珍的悉心照顾,父亲才恢复得很快。谢京福也知道,做这些是应该的。但是看到父亲与兰姨总是在一边嘀咕什么“结婚”,心里又觉得郁闷。
但是,他与曹慧珍踏入这家店铺的瞬间,就惊呆了。只见这件店铺装修得极为高贵典雅,古画、紫檀与文竹的相配,无一不体现了主人的情趣。他也看到了,里边有两个穿着统一制服的女店员,还有一个姑娘穿着一条缀满了白色小雏菊花的花布裙子,一头长发也编成了辫子,盘在脑后。北京的街道上开始偶尔会看到一些穿着这裙子的苏联女人。后来便看到很多中国姑娘也不再穿那些军装了。这裙子穿在她的身上很美,那窈窕的腰身系了一条腰带,裙摆摇曳,笑靥如花。
谢京福脚下的步子再也迈不动了,他只看一眼,便知道那是伊杭。他甚至不敢相信不过几天没见,伊杭就活脱脱从一个宅在院子的贵族格格变成了伶俐俏皮的女商人。
“这丝绸可以做一件和我身上的这件相同样式的裙子,叫布拉吉,非常好看,现在老北京的人们经济缓和了,姑娘们做件漂亮衣服也是承受的了,主要是我们的杭州丝绸柔滑细腻,太美了,不做一件真是可惜了。”
一个梳着两只辫子的姑娘有些腼腆地看着身边的母亲,有些犹豫不决。那眼神里明明都是羡慕,但是似乎还是不敢第一个出来“吃螃蟹”。
母亲也开心地摸着那些丝绸:“好不容易搞来些布票,这不就省着想给女儿做嫁妆了。只是,我这闺女还真是没主意。”
“这样吧!”只见伊杭抿着嘴笑了笑,拿出了纸和笔,只在纸上飞速地勾画了片刻,只见一条缀满了玫瑰花的礼服裙赫然呈现在纸上,看着母女两人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看不出来,姑娘你可是个才女,还会设计样式,谁娶了你真是有福气。”母亲看着画上的礼服裙连连点头,“闺女,我和你爸都是开明人,现在都是新国家了,更要有新气象。这么好的杭州丝绸可不能辜负了,咱就做些新样式,妈也不穿这件老革命了。”做母亲的,抚摸着自己身上的一件蓝色列宁装,摇头说。
“好,我再去拿些样板,如果喜欢,就先订下来。”伊杭转身,开心地吩咐店员去拿里间新来的样板。
但是,她转身却看到了一个身穿一套欧式套裙,头发烫着大波浪卷,手中提着一只精美的缎面绣花口金包,另一只手却夹着一支法国雪茄的四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淡淡的笑容似乎藏着世事沧桑里最诡异的心机。
只见她颐指气使地指着里边的贵宾室说:“怎么?既然看到长辈到了,怎么还不请长辈进去坐坐?”
伊杭有些紧张,连忙吩咐店员照顾好客人,自己走了过来:“凌云阿姨来了,里边请。凌云阿姨,这里是丝绸店,不允许吸烟,请您……”
谢京福忽然看不到伊杭了,心莫名慌乱了起来,耳边听到曹慧珍的声音:“福哥,你怎么还不进来?帮我挑两块丝绸吧!”
谢京福应了一声,刚刚进入店门,就看到那个叫凌云的女人,从屋子里气冲冲地走了出来,大声嚷着:“好啊,既然给你们脸,你们不要,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就是让这里的人都听听,你们傅家都做了什么!”
伊杭窘红了脸,看了看四周惊奇寻过来的眼光,更加不安了。
那凌云却得理不饶人,指着店里那块写着“诚信经营”四个字的牌子,不屑一顾地说:“明明是鸠占鹊巢,占着别人的家产不还,还好意思说什么‘诚信’这两个字!伊杭,既然你这么有本事,还不如速战速决,赶紧把傅家的财产交出来。”
伊杭看到不能制止凌云的挑衅,索性豁了出去,说:“凌云阿姨,即便这房产将来是要落在我哥哥的名下,但是现在我阿玛还在世,也不能现在就分家产。再说,您找到了我的店里这样闹,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凌云“喷”了一口香烟,冷笑着说:“看你这伶牙俐齿的,幸亏我有备而来。你那个该死的阿玛现在喝得连人都认不清楚了,你额娘又是个病秧子,让我找谁去说理去。”
“可是……到现在我也没听过大哥的消息,让我怎么能相信您?”伊杭每听到这女人的声音,心里便不寒而栗。
富察氏如果还有过去的荣耀,这样的女人都是不屑于看一眼的人。她是父亲的大福晋的叔伯妹妹凌云,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如桃花、心如蛇蝎的凶狠角色。娶了母亲之后,大福晋生了场病,竟然闹得几乎要出人命。那时,就是这个叫凌云的女人亲手撕扯着母亲的头发,骂她是“狐狸精、害人精”,将富察氏的尊严践踏的一无是处。自那时起,要面子的父亲告诫家人,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提我们是富察氏的后人,在外边只能用汉姓“傅”字。
凌云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姑娘说出来的话却一点儿都不气馁,反而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清高,不由声音又提高了几分:“我早就知道你这丫头不像表面这样弱不禁风,你看这是什么?”
凌云递过来的是一封信。
伊杭犹豫了一下,心想躲避终究不是办法,还是看一看再说。她伸出纤细的手指,接过了那封信。原来那果真是兄长给凌云阿姨的代理授权书,让凌云阿姨全权处理他名下的财产。
她轻轻一笑:“凌云阿姨,我母亲也算是父亲认下的妾室,就算是分家产,也有我额娘的份额,所以这个宅子是不能给您的。”
“那好,就照之前我的提议,将院子一份为二,各自过活,怎么样?”
伊杭摇头:“等我回去问过阿玛额娘再答复你。”
凌云“哎呀”一声,站了起来。由于脚下穿着高跟鞋,起的太急,站立不稳,险些栽倒。倒是伊杭不计前嫌,搀扶了她一把。她不领情,只是狠狠将伊杭的手甩了出去:“我说你这丫头片子,主意还真是正得很,真是我小瞧你了。我看你趁着现在还能给你出些嫁妆,早点找个像样的男人嫁了,省得将来一无所得,后悔一辈子。”
“我的终身大事,就不劳您老人家操心了。”
这一句话,仿佛勾起了凌云的满腔怒火,她指着伊杭的脸,歇斯底里地骂起来:“得意什么?不是就个杭州裁缝家的闺女攀了高枝,还以为自己真的飞上枝头当凤凰了?我看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给自己留点后路,省得将来没人可怜!”
伊杭看着店里进来越来越多的人,有的是来买丝绸的,有的却是来看热闹的,不由脸和脖子都红了。她低眉敛目,小声说:“麻烦您给腾个地方吧!这里还是要做生意的,您多积德行善,是会有好报的。
伊杭的话音未落,只听得“嘶啦”一声,看到自己的衣领被蛮横的凌云撕裂,她的脸红了,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听到“啪”一声,顿时觉得自己的右脸也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只听到凌云横眉立目地喊着:“我就是欺负你,又能怎么样?啊,大家听听,我是来讨债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谢京福看着伊杭捂着自己的衣领,由于羞怒已经泪水满眶,他的胸口已经波涛汹涌,两只手暗自攥起了拳头,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想挡在伊杭面前。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身边的曹慧珍扒拉开众人,冲上去朝着凌云“啪”一掌就还了回去。
凌云急怒喊道:“什么人?敢打我?”
曹慧珍昂着头,冷冷一笑,不屑一顾地说:“是我,我叫曹慧珍,曹操的曹,聪慧的慧,珍宝的珍,记住了!就我打你的,怎么样?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人家在这里好端端的做生意,又没招你惹你,你明明就是来挑衅的。我曹慧珍也是个侠肝义胆的女子,素来就看不惯你这种欺负人的人。今天,我就替这个小姑娘打抱不平,怎么样?你去法院,去公安局,告我去!我看谁怕谁?”
凌云捂着脸,被曹慧珍的气势逼退了几步,她有些胆怯地说:“你是哪根葱?傅家的事情轮的上你管?”
曹慧珍叉着腰,朝凌云笑道:“你又是哪根葱?这个什么傅家的事和你又关系?你非嫡非长、非亲非故,什么时候轮的上你管人家的事了?我看你就是仗势欺人的女魔头!”
凌云气急败坏地跳着脚,却再也不敢上前,只好气呼呼地提起自己的手包,朝外走去:“好,有你的,咱们走着瞧!”
曹慧珍朝凌云远去的背影“唾”了一口,朝着四周窥探的人群叫着:“看什么看,你认识你家姑奶奶?去去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挡着人家做生意。”
她想起和自己同来的谢京福,转头发现,他站在那蹲着委屈哭泣的姑娘身边,将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轻轻披在那姑娘的身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此刻,一缕阳光从明亮的玻璃窗上飘了下来,正好投在两个人身上。
眼前的两个人,一个是梨花带雨、娇柔妩媚,一个小心翼翼、侠骨柔情。端的是一副痴男怨女的凄美画面。谢京福呆呆站立着,丝毫听不到自己的呼唤,那专注的眼神,像极了他做珐琅时的样子。她知道,那个时候,无论有人说什么,他都是听不到的。而那个姑娘,似乎早已经与谢京福熟识,口中低声叫了一句:“谢大哥。”便又低头嘤嘤哭泣,似乎有无穷的心事,令人顿生怜悯之心。
她呆了,心中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绝望开始涌了上来。这些日子,她的心里眼里只有谢京福一个人,他的每一个动作,甚至呼吸她都熟悉到五脏六腑,说不出为什么,她莫名有了危机感,这种感觉似乎随时会将自己前生今世的努力彻底颠覆,她忽然间卸掉了刚才那铁齿铜牙般的外表,安静了下来。
她觉得,此刻的谢京福,是她所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
那姑娘哭了很久,终于停了下来,她似乎和谢京福说了些什么,谢京福的脸色这才松弛下来。
此情此景,让曹慧珍心生绝望继而浑浑噩噩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谢京福将她拉回到家门口,她才醒悟过来,自己有些失态了。谢京福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没买成衣料,改天我们再买。”
曹慧珍觉得自己的脚步软软的,口中也说不出什么,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没事,这大半天的了,谢大爷还在家里,不知道吃没吃饭,赶紧回去看看吧!”
谢京福应了一声,调转了身子,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曹慧珍看着谢京福走得铿锵有力的步子,感觉自己的气力渐渐消失。她想起了这些日子,在谢京福的屋子里,看到有很多用毛笔写的娟秀字迹,还有谢京福自己歪歪扭扭写的字,那些字并不是《识字课本》里的,有时还似乎是一句古诗什么的,不知道他这些字句都是跟谁学的,但是可以确信,他身后必定有个知书达理的姑娘正在教授他。谢京福屡次拒绝了自己与他相处的机会,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写那字的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样的结果着实可怕。
谢京福与曹慧珍一前一后,往里边瞧着,挤过了一群又一群人。这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曹慧珍第一次来,兴奋地转着,忽然指着前边一家写着“杭州丝绸分店”的店面,笑着说:“福哥,我们去那里吧!”
谢京福无奈,只好答应。父亲让自己带着曹慧珍来买块上等的料子,这些天都是曹慧珍的悉心照顾,父亲才恢复得很快。谢京福也知道,做这些是应该的。但是看到父亲与兰姨总是在一边嘀咕什么“结婚”,心里又觉得郁闷。
但是,他与曹慧珍踏入这家店铺的瞬间,就惊呆了。只见这件店铺装修得极为高贵典雅,古画、紫檀与文竹的相配,无一不体现了主人的情趣。他也看到了,里边有两个穿着统一制服的女店员,还有一个姑娘穿着一条缀满了白色小雏菊花的花布裙子,一头长发也编成了辫子,盘在脑后。北京的街道上开始偶尔会看到一些穿着这裙子的苏联女人。后来便看到很多中国姑娘也不再穿那些军装了。这裙子穿在她的身上很美,那窈窕的腰身系了一条腰带,裙摆摇曳,笑靥如花。
谢京福脚下的步子再也迈不动了,他只看一眼,便知道那是伊杭。他甚至不敢相信不过几天没见,伊杭就活脱脱从一个宅在院子的贵族格格变成了伶俐俏皮的女商人。
“这丝绸可以做一件和我身上的这件相同样式的裙子,叫布拉吉,非常好看,现在老北京的人们经济缓和了,姑娘们做件漂亮衣服也是承受的了,主要是我们的杭州丝绸柔滑细腻,太美了,不做一件真是可惜了。”
一个梳着两只辫子的姑娘有些腼腆地看着身边的母亲,有些犹豫不决。那眼神里明明都是羡慕,但是似乎还是不敢第一个出来“吃螃蟹”。
母亲也开心地摸着那些丝绸:“好不容易搞来些布票,这不就省着想给女儿做嫁妆了。只是,我这闺女还真是没主意。”
“这样吧!”只见伊杭抿着嘴笑了笑,拿出了纸和笔,只在纸上飞速地勾画了片刻,只见一条缀满了玫瑰花的礼服裙赫然呈现在纸上,看着母女两人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看不出来,姑娘你可是个才女,还会设计样式,谁娶了你真是有福气。”母亲看着画上的礼服裙连连点头,“闺女,我和你爸都是开明人,现在都是新国家了,更要有新气象。这么好的杭州丝绸可不能辜负了,咱就做些新样式,妈也不穿这件老革命了。”做母亲的,抚摸着自己身上的一件蓝色列宁装,摇头说。
“好,我再去拿些样板,如果喜欢,就先订下来。”伊杭转身,开心地吩咐店员去拿里间新来的样板。
但是,她转身却看到了一个身穿一套欧式套裙,头发烫着大波浪卷,手中提着一只精美的缎面绣花口金包,另一只手却夹着一支法国雪茄的四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淡淡的笑容似乎藏着世事沧桑里最诡异的心机。
只见她颐指气使地指着里边的贵宾室说:“怎么?既然看到长辈到了,怎么还不请长辈进去坐坐?”
伊杭有些紧张,连忙吩咐店员照顾好客人,自己走了过来:“凌云阿姨来了,里边请。凌云阿姨,这里是丝绸店,不允许吸烟,请您……”
谢京福忽然看不到伊杭了,心莫名慌乱了起来,耳边听到曹慧珍的声音:“福哥,你怎么还不进来?帮我挑两块丝绸吧!”
谢京福应了一声,刚刚进入店门,就看到那个叫凌云的女人,从屋子里气冲冲地走了出来,大声嚷着:“好啊,既然给你们脸,你们不要,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就是让这里的人都听听,你们傅家都做了什么!”
伊杭窘红了脸,看了看四周惊奇寻过来的眼光,更加不安了。
那凌云却得理不饶人,指着店里那块写着“诚信经营”四个字的牌子,不屑一顾地说:“明明是鸠占鹊巢,占着别人的家产不还,还好意思说什么‘诚信’这两个字!伊杭,既然你这么有本事,还不如速战速决,赶紧把傅家的财产交出来。”
伊杭看到不能制止凌云的挑衅,索性豁了出去,说:“凌云阿姨,即便这房产将来是要落在我哥哥的名下,但是现在我阿玛还在世,也不能现在就分家产。再说,您找到了我的店里这样闹,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凌云“喷”了一口香烟,冷笑着说:“看你这伶牙俐齿的,幸亏我有备而来。你那个该死的阿玛现在喝得连人都认不清楚了,你额娘又是个病秧子,让我找谁去说理去。”
“可是……到现在我也没听过大哥的消息,让我怎么能相信您?”伊杭每听到这女人的声音,心里便不寒而栗。
富察氏如果还有过去的荣耀,这样的女人都是不屑于看一眼的人。她是父亲的大福晋的叔伯妹妹凌云,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如桃花、心如蛇蝎的凶狠角色。娶了母亲之后,大福晋生了场病,竟然闹得几乎要出人命。那时,就是这个叫凌云的女人亲手撕扯着母亲的头发,骂她是“狐狸精、害人精”,将富察氏的尊严践踏的一无是处。自那时起,要面子的父亲告诫家人,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提我们是富察氏的后人,在外边只能用汉姓“傅”字。
凌云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姑娘说出来的话却一点儿都不气馁,反而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清高,不由声音又提高了几分:“我早就知道你这丫头不像表面这样弱不禁风,你看这是什么?”
凌云递过来的是一封信。
伊杭犹豫了一下,心想躲避终究不是办法,还是看一看再说。她伸出纤细的手指,接过了那封信。原来那果真是兄长给凌云阿姨的代理授权书,让凌云阿姨全权处理他名下的财产。
她轻轻一笑:“凌云阿姨,我母亲也算是父亲认下的妾室,就算是分家产,也有我额娘的份额,所以这个宅子是不能给您的。”
“那好,就照之前我的提议,将院子一份为二,各自过活,怎么样?”
伊杭摇头:“等我回去问过阿玛额娘再答复你。”
凌云“哎呀”一声,站了起来。由于脚下穿着高跟鞋,起的太急,站立不稳,险些栽倒。倒是伊杭不计前嫌,搀扶了她一把。她不领情,只是狠狠将伊杭的手甩了出去:“我说你这丫头片子,主意还真是正得很,真是我小瞧你了。我看你趁着现在还能给你出些嫁妆,早点找个像样的男人嫁了,省得将来一无所得,后悔一辈子。”
“我的终身大事,就不劳您老人家操心了。”
这一句话,仿佛勾起了凌云的满腔怒火,她指着伊杭的脸,歇斯底里地骂起来:“得意什么?不是就个杭州裁缝家的闺女攀了高枝,还以为自己真的飞上枝头当凤凰了?我看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给自己留点后路,省得将来没人可怜!”
伊杭看着店里进来越来越多的人,有的是来买丝绸的,有的却是来看热闹的,不由脸和脖子都红了。她低眉敛目,小声说:“麻烦您给腾个地方吧!这里还是要做生意的,您多积德行善,是会有好报的。
伊杭的话音未落,只听得“嘶啦”一声,看到自己的衣领被蛮横的凌云撕裂,她的脸红了,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听到“啪”一声,顿时觉得自己的右脸也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只听到凌云横眉立目地喊着:“我就是欺负你,又能怎么样?啊,大家听听,我是来讨债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谢京福看着伊杭捂着自己的衣领,由于羞怒已经泪水满眶,他的胸口已经波涛汹涌,两只手暗自攥起了拳头,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想挡在伊杭面前。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身边的曹慧珍扒拉开众人,冲上去朝着凌云“啪”一掌就还了回去。
凌云急怒喊道:“什么人?敢打我?”
曹慧珍昂着头,冷冷一笑,不屑一顾地说:“是我,我叫曹慧珍,曹操的曹,聪慧的慧,珍宝的珍,记住了!就我打你的,怎么样?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人家在这里好端端的做生意,又没招你惹你,你明明就是来挑衅的。我曹慧珍也是个侠肝义胆的女子,素来就看不惯你这种欺负人的人。今天,我就替这个小姑娘打抱不平,怎么样?你去法院,去公安局,告我去!我看谁怕谁?”
凌云捂着脸,被曹慧珍的气势逼退了几步,她有些胆怯地说:“你是哪根葱?傅家的事情轮的上你管?”
曹慧珍叉着腰,朝凌云笑道:“你又是哪根葱?这个什么傅家的事和你又关系?你非嫡非长、非亲非故,什么时候轮的上你管人家的事了?我看你就是仗势欺人的女魔头!”
凌云气急败坏地跳着脚,却再也不敢上前,只好气呼呼地提起自己的手包,朝外走去:“好,有你的,咱们走着瞧!”
曹慧珍朝凌云远去的背影“唾”了一口,朝着四周窥探的人群叫着:“看什么看,你认识你家姑奶奶?去去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挡着人家做生意。”
她想起和自己同来的谢京福,转头发现,他站在那蹲着委屈哭泣的姑娘身边,将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轻轻披在那姑娘的身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此刻,一缕阳光从明亮的玻璃窗上飘了下来,正好投在两个人身上。
眼前的两个人,一个是梨花带雨、娇柔妩媚,一个小心翼翼、侠骨柔情。端的是一副痴男怨女的凄美画面。谢京福呆呆站立着,丝毫听不到自己的呼唤,那专注的眼神,像极了他做珐琅时的样子。她知道,那个时候,无论有人说什么,他都是听不到的。而那个姑娘,似乎早已经与谢京福熟识,口中低声叫了一句:“谢大哥。”便又低头嘤嘤哭泣,似乎有无穷的心事,令人顿生怜悯之心。
她呆了,心中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绝望开始涌了上来。这些日子,她的心里眼里只有谢京福一个人,他的每一个动作,甚至呼吸她都熟悉到五脏六腑,说不出为什么,她莫名有了危机感,这种感觉似乎随时会将自己前生今世的努力彻底颠覆,她忽然间卸掉了刚才那铁齿铜牙般的外表,安静了下来。
她觉得,此刻的谢京福,是她所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
那姑娘哭了很久,终于停了下来,她似乎和谢京福说了些什么,谢京福的脸色这才松弛下来。
此情此景,让曹慧珍心生绝望继而浑浑噩噩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谢京福将她拉回到家门口,她才醒悟过来,自己有些失态了。谢京福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没买成衣料,改天我们再买。”
曹慧珍觉得自己的脚步软软的,口中也说不出什么,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没事,这大半天的了,谢大爷还在家里,不知道吃没吃饭,赶紧回去看看吧!”
谢京福应了一声,调转了身子,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曹慧珍看着谢京福走得铿锵有力的步子,感觉自己的气力渐渐消失。她想起了这些日子,在谢京福的屋子里,看到有很多用毛笔写的娟秀字迹,还有谢京福自己歪歪扭扭写的字,那些字并不是《识字课本》里的,有时还似乎是一句古诗什么的,不知道他这些字句都是跟谁学的,但是可以确信,他身后必定有个知书达理的姑娘正在教授他。谢京福屡次拒绝了自己与他相处的机会,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写那字的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样的结果着实可怕。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