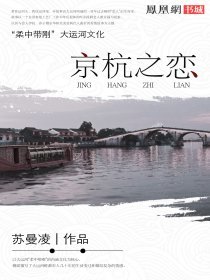第六章 柳暗花明2
这日午后,谢慎休息了约半个小时,便拄着拐杖朝院子里的天空望着,几只鸽子在空中划出了几道白线,白云写意般地点缀在蓝色的“幕布”上,有了几分水墨画的神韵。他伸出手,拇指还是僵硬得很,不由微微又叹了口气,他刚刚吃完曹慧珍送来的馄饨,说一会儿过来拿碗。他已经发现,那姑娘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似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子不在家,又去什刹海跑黄包车去了。
只想了一会儿,就看到曹慧珍进了屋。她拿起了碗,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而是低头问了一句:“大爷,我做得馄饨味道怎么样?”
“那还用说?薄皮大馅,入口就闻到了香菜混入虾皮的味道,别提有多正宗了。”
曹慧珍的眼皮没有抬起来,只是唏嘘了一口,继续说道:“可是,怕是以后您就吃不到我做的馄饨了。”
谢慎大吃一惊:“为什么?”
“我母亲的身体近来也不算太好,所以我打算回去照顾她一阵子,这样,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百善孝为先,慧珍,你这个想法是对的。该回去就回去,不要考虑我这个老家伙。以后还可以回来的。”
曹慧珍的眼眶涌满了泪水,她摇摇头:“我母亲说,我也不小了,该早点定下个人的事情,这次回去,有人给我提了一门亲事,是个教授,很有学问。我也想考虑一下。”
谢慎听的出姑娘是婉转地试探自己的心意,连忙说:“是不是京福这孩子又惹你不高兴了?”
“我觉得,谢大哥心里可能有人了,不是我。既然他不喜欢我,我也该自己又自知之明,早点回去。”
“什么?”谢慎听到曹慧珍这样说,忽然闷声大笑起来,“谢京福那孩子,是根榆木疙瘩,看到姑娘都脸红,哪里会懂得这些情情爱爱的,你不赶着他走,他都会在原地蹲着不动弹。”
“不,谢大哥看那丝绸店女经理的眼神是不同的,我看的出来,那是爱情,和别人的不一样。”
“丝绸店女经理?”谢慎惊了一下,“谢京福很少出门,也就只是偶尔去傅家几趟,怎么会认识丝绸店女经理,闺女,你是想多了。”
“谢大爷,我真的感觉那眼神是和看我的不一样,您说的是,那姑娘好像是姓傅的……那姓傅的姑娘被人给欺负了,他可是维护得紧。”
“姓傅?”谢慎的话打了磕,他翻着眼皮想了想,“难道真的是那丫头?不过,那丫头和京福差了快二十岁了大概,怎么可能?京福自小就是个善良的孩子,他一定是看那姑娘受了委屈,同情心上来了。慧珍呀,我看真是你想多了。”
“是么?”曹慧珍抿了抿嘴,将碗端正了,朝谢慎说,“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和三姨商量一下再决定。”
谢慎看着曹慧珍怅然若失地离开了,转悠着看着儿子屋里乱七八糟的铜皮屑,桌子上还有一个“春江水暖”的六棱瓶的胎体,掐丝刚刚到一半,上边的几只野鸭还没有上全。碟子里的白芨已经半干了,似乎有一阵子没有做过了。他叹了口气,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天色渐渐昏黄,他看到儿子风尘仆仆拉着黄包车回了家,也心疼儿子知道家中经济拮据,而出去跑车。但是这婚事真不能再拖下去,怕一拖就又是大半年过去了。
“您老人家的药吃了?”谢京福放下车,来不及洗脸换衣服,先看看今天父亲的药都不在了,庆幸父亲终于听话按时吃药了。
谢慎闭上了眼,半躺在了外间的竹椅上。没有和以往一样训斥儿子,教他做珐琅和怎么修复那些珐琅器的窍门,而是说:“儿子,我有个不可告人的隐秘之事,横隔在心头二十多年了。我这一病,我忽然间想明白了很多事。富贵贫穷,都是我们不可以选择的命运,硬是要违背天道良心,就会得到报应。”
谢京福也很奇怪父亲今日的神情,默默地将脏污的外衣脱了下来,用门口的铜盆舀了两勺水,呼啦呼啦洗起了脸。
谢慎却没有管儿子在做什么,只是一字一句地说着:“这辈子,我谢慎也算是光明磊落的汉子,唯独对傅家,我是存了私心的。”
谢京福忽然听到“傅家”这个词,便停了下来,用毛巾擦干了自己的脸,仔细倾听。他不解地看到父亲眼睛里泪光闪烁,正唏嘘着,仿佛在忏悔什么:“你去我屋的柜子,把最下边的木盒子拿出来。”
谢京福按照父亲的吩咐找出了那个红盒子。那是一款雕花紫檀木盒,上边雕刻得牡丹惟妙惟肖,一看就知道是出自有经验的老匠师之手。打开它,里边是一层厚厚的锦缎。谢京福看到眼前忽然出现了三颗硕大的缅甸鸽血红宝石,那宝石打磨得熠熠生辉,昏暗的屋子也由于这三颗红宝石的出现亮堂起来。
“这是?”
谢慎笑了,却笑得比哭还难看。“这是现在傅家主人的父亲,当年的珲贝子亲手交到我手里的,让我偷偷给子孙后代们做些好东西,这些红宝石就是用来镶嵌在上边的宝贝。我本是感激珲贝子的信任,可是没想到那年珲贝子忽然就殁了。于是,这三颗红宝石便成了我私藏的珍品,傅家子孙无人知道。我自小就看到你祖父、曾祖父给傅家做牛做马,心中就想,为什么我家就天生是家仆,而傅家天生就是主人,他们凭什么可以将我们谢家的人任意驱使。所以,我便将这件事沉了下来。”
谢京福听得有些心痛,他悄悄问:“这也是您这些年寝食不安的缘由?”
谢慎点头:“不错,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个理儿。三个月前,我无意中到西四转悠,看到傅家的主人被人头上扣满了白菜叶子,有人说,如果是当年大清朝,谁敢欺负他呀,那是要灭九族的。有人还说,现在是树倒猢狲散,只要有点本事的,都可以欺负他。还有人说,做了亏心事,死了也就没了魂魄。我回来,想了想,我是不是做错了?”
谢京福扶着谢慎摇摇欲坠的身子,说:“这些东西既不是我们的,勉强藏匿起来,这辈子也不敢拿出来示人,且良心难安,不是吗?”
谢慎老泪纵横起来:“不错。我枉为人父,我口口声声交教导你们,为人要干净纯良,才能做好珐琅,可现在我却这样糊涂……”
“我知道了,您放心,我这就拿去还给傅家。”谢京福终于明白原来父亲藏了这样的私心,也因为此事曾经殚精竭虑地以图心安,最终还是难以逾越良心之谴。
他看到父亲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也深深理解父亲的心意。他告诉自己,要好好满足老人家的心愿,不再忤逆了。
他也没有想到,再次踏入傅家,竟然是由于谢家的过错。他反复演练了多次对这件事的说辞,一路忐忑不安的,一想到要面对伊杭的面,说出这些,还是有些难以启齿。他走进傅家,听到的是里边喧闹的人声,隐隐还有傅恒远的怒骂声和伊杭的哭声,他暗道一声:“不好。”便冲进了院子。
果然,院子里的花草被践踏成泥,水缸也被砸成了两瓣。傅恒远趴在屋檐下,凌乱的头发上到处是脏水,他捂着自己的右腿,低声呻吟着。而伊杭正朝那些人鞠躬:“请宽限几天吧!我一定想办法还上钱。”
为首的一个男子,看着伊杭吹弹可破的肌肤,一把抬起伊杭的下颚,嘿嘿笑道:“你这小模样倒是不错,要是你肯跟了我,我就免了你家的债,还给你娘出医药费,怎么样?”
伊杭怒意地挣脱了那男子的桎梏,朝他说:“如果你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那男子“喝”了一声:“还挺厉害,我看你能够厉害到什么时候?”
他说着,伸出手就拉扯伊杭,伊杭朝后退去,但是当她再抬头看到,谢京福已经拦住了那男子。
男子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子我混江湖也多年了,从来都是我当护花使者,今天怎么还来了插一杠子的?”
谢京福郑重其事的说:“如果你敢再动他们一根手指头,我就去公安局告你们,现在是法制社会,不是过去混江湖的旧社会了,难道你们以为国家的法制还真是说着玩的。”
那男子怒笑:“别拿那些公检法吓唬老子,老子不怕!”
此刻,他后边的几个人凑过来小声说:“大哥,我们只是来要债的,不是来要人命的。别忘了上次你在公安局签了保证书的,可不要因小失大了!”
男子思索了片刻,挥了挥手,指着傅恒远说:“好吧,我告诉你,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你如果再不换钱,我就烧了你家这宅子!”
傅恒远“哼”着:“你烧了这房子,我拿什么还债?”
男子不甘心地往外走,说道:“你自己想想,欠债不还,总是要有个说法。”他说完,示意自己的人离开。
傅恒远斜着眼睛看着这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才壮起胆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谢家小子,你又来了,我家可不欠你工钱,你来做什么?”
谢京福捏了捏裤兜里的盒子,心想这东西还是不能交给傅恒远,否则怕是一去不回,于是点头说:“我爹说时间不短了,让我过来问问,傅家还有什么活要做的?”
“还算你们有良心,哦呵……”傅恒远呻吟着,摸着自己的臀部,“如果你们谢家还记挂着我们傅家对你们的恩情,现在也该站出来偿还了,是不是要拿些钱出来先顶顶风声呢?”
谢京福不知道怎么回复这话,只好闷声不语。
“阿玛!”伊杭听了这话,心中悲愤,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到了现在你还说这样大言不惭的话,难道你真的想让我和额娘都无家可归吗?想让每一个和我们的傅家有关系的人都以你为耻吗?真是想把我们这个家最后一点儿脸面都丢尽吗?”
“你这丫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傅恒远歪着嘴,不乐意地说,“我现在是走到哪里都被人嫌,是不是你们也嫌弃我了?”
“阿玛?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和我额娘都被你给逼成什么样子了?我额娘她……都病得这样重了,你居然一点儿都不顾她,你到底长没长心啊?”
傅恒远似乎还沉浸在昨日的宿醉里,他眯着眼睛,说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还是钱有用,谁给我钱,让我管谁叫祖宗都成,我连自己的都保不住,哪里还有能力来保你们?对了,丫头,你最近生意不是做得风声水起,你挣的钱呢?还不拿出些孝敬你阿玛?”
这话说得无情无义,谢京福觉得自己都浑身颤抖了几下,他慌乱地看着伊杭的脸色越来越惨白,明显已经被自己父亲气得几乎晕厥,他忽然很想做些什么,便对傅恒远说:“您还是顾些情义吧?毕竟这是您的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傅恒远似乎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他翻过身子,轻哼一声,说道,“说起这事来,还是真得细细琢磨一下,当年你额娘也是和她那个表哥是订了亲的,两个人暧昧得很,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呢?不过是我胸襟大,不计较罢了!”
听着这话,伊杭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嘤嘤哭泣起来。
谢京福一看到伊杭伤心,就有些抑制不住,他的脸色变了,深深呼吸了一口,鼓起了勇气,想和这傅家主人理论一番。
“傅恒远,你好狠心!”谢京福看到门口站着那面色晦暗的侧福晋水莲,她扶着门框,一边喘息着,一边指着傅恒远说,“我跟了你这么多年,千难万难,千苦万苦,我都能受的,只是因为心里还牵挂着你对我的一份情意,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心思,我真是悔不该当初没听父母的话,才有了今天的报应,我活该!我该千刀万剐!但是,你不要侮辱我们的孩子,她是堂堂正正的满族格格,她骨子里都是高贵的气质,这是你用多少肮脏的语言都淹没不了的!傅恒远,我看透了你,从今天开始,我只有女儿,没有丈夫!”
她说完,又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很快就颓靡地倒了下去。伊杭大声喊着“额娘”,便冲了过去。谢京福也赶紧过去,搀扶起侧福晋。
只见侧福晋水莲的眼皮不停地煽动着,她孱弱地攥紧自己女儿的手,说:“孩子,去找你表舅去,离开这里,去杭州找你的外祖母,不然,怕是这个家要害死你!”
这话说完,她便垂下了手,闭上了眼睛,再无声息。伊杭看到母亲手中的帕子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忽然有种即将失去的恐惧感,她不由大声喊着:“额娘,你醒醒,我不要你死!不要!”
只想了一会儿,就看到曹慧珍进了屋。她拿起了碗,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而是低头问了一句:“大爷,我做得馄饨味道怎么样?”
“那还用说?薄皮大馅,入口就闻到了香菜混入虾皮的味道,别提有多正宗了。”
曹慧珍的眼皮没有抬起来,只是唏嘘了一口,继续说道:“可是,怕是以后您就吃不到我做的馄饨了。”
谢慎大吃一惊:“为什么?”
“我母亲的身体近来也不算太好,所以我打算回去照顾她一阵子,这样,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百善孝为先,慧珍,你这个想法是对的。该回去就回去,不要考虑我这个老家伙。以后还可以回来的。”
曹慧珍的眼眶涌满了泪水,她摇摇头:“我母亲说,我也不小了,该早点定下个人的事情,这次回去,有人给我提了一门亲事,是个教授,很有学问。我也想考虑一下。”
谢慎听的出姑娘是婉转地试探自己的心意,连忙说:“是不是京福这孩子又惹你不高兴了?”
“我觉得,谢大哥心里可能有人了,不是我。既然他不喜欢我,我也该自己又自知之明,早点回去。”
“什么?”谢慎听到曹慧珍这样说,忽然闷声大笑起来,“谢京福那孩子,是根榆木疙瘩,看到姑娘都脸红,哪里会懂得这些情情爱爱的,你不赶着他走,他都会在原地蹲着不动弹。”
“不,谢大哥看那丝绸店女经理的眼神是不同的,我看的出来,那是爱情,和别人的不一样。”
“丝绸店女经理?”谢慎惊了一下,“谢京福很少出门,也就只是偶尔去傅家几趟,怎么会认识丝绸店女经理,闺女,你是想多了。”
“谢大爷,我真的感觉那眼神是和看我的不一样,您说的是,那姑娘好像是姓傅的……那姓傅的姑娘被人给欺负了,他可是维护得紧。”
“姓傅?”谢慎的话打了磕,他翻着眼皮想了想,“难道真的是那丫头?不过,那丫头和京福差了快二十岁了大概,怎么可能?京福自小就是个善良的孩子,他一定是看那姑娘受了委屈,同情心上来了。慧珍呀,我看真是你想多了。”
“是么?”曹慧珍抿了抿嘴,将碗端正了,朝谢慎说,“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和三姨商量一下再决定。”
谢慎看着曹慧珍怅然若失地离开了,转悠着看着儿子屋里乱七八糟的铜皮屑,桌子上还有一个“春江水暖”的六棱瓶的胎体,掐丝刚刚到一半,上边的几只野鸭还没有上全。碟子里的白芨已经半干了,似乎有一阵子没有做过了。他叹了口气,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天色渐渐昏黄,他看到儿子风尘仆仆拉着黄包车回了家,也心疼儿子知道家中经济拮据,而出去跑车。但是这婚事真不能再拖下去,怕一拖就又是大半年过去了。
“您老人家的药吃了?”谢京福放下车,来不及洗脸换衣服,先看看今天父亲的药都不在了,庆幸父亲终于听话按时吃药了。
谢慎闭上了眼,半躺在了外间的竹椅上。没有和以往一样训斥儿子,教他做珐琅和怎么修复那些珐琅器的窍门,而是说:“儿子,我有个不可告人的隐秘之事,横隔在心头二十多年了。我这一病,我忽然间想明白了很多事。富贵贫穷,都是我们不可以选择的命运,硬是要违背天道良心,就会得到报应。”
谢京福也很奇怪父亲今日的神情,默默地将脏污的外衣脱了下来,用门口的铜盆舀了两勺水,呼啦呼啦洗起了脸。
谢慎却没有管儿子在做什么,只是一字一句地说着:“这辈子,我谢慎也算是光明磊落的汉子,唯独对傅家,我是存了私心的。”
谢京福忽然听到“傅家”这个词,便停了下来,用毛巾擦干了自己的脸,仔细倾听。他不解地看到父亲眼睛里泪光闪烁,正唏嘘着,仿佛在忏悔什么:“你去我屋的柜子,把最下边的木盒子拿出来。”
谢京福按照父亲的吩咐找出了那个红盒子。那是一款雕花紫檀木盒,上边雕刻得牡丹惟妙惟肖,一看就知道是出自有经验的老匠师之手。打开它,里边是一层厚厚的锦缎。谢京福看到眼前忽然出现了三颗硕大的缅甸鸽血红宝石,那宝石打磨得熠熠生辉,昏暗的屋子也由于这三颗红宝石的出现亮堂起来。
“这是?”
谢慎笑了,却笑得比哭还难看。“这是现在傅家主人的父亲,当年的珲贝子亲手交到我手里的,让我偷偷给子孙后代们做些好东西,这些红宝石就是用来镶嵌在上边的宝贝。我本是感激珲贝子的信任,可是没想到那年珲贝子忽然就殁了。于是,这三颗红宝石便成了我私藏的珍品,傅家子孙无人知道。我自小就看到你祖父、曾祖父给傅家做牛做马,心中就想,为什么我家就天生是家仆,而傅家天生就是主人,他们凭什么可以将我们谢家的人任意驱使。所以,我便将这件事沉了下来。”
谢京福听得有些心痛,他悄悄问:“这也是您这些年寝食不安的缘由?”
谢慎点头:“不错,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个理儿。三个月前,我无意中到西四转悠,看到傅家的主人被人头上扣满了白菜叶子,有人说,如果是当年大清朝,谁敢欺负他呀,那是要灭九族的。有人还说,现在是树倒猢狲散,只要有点本事的,都可以欺负他。还有人说,做了亏心事,死了也就没了魂魄。我回来,想了想,我是不是做错了?”
谢京福扶着谢慎摇摇欲坠的身子,说:“这些东西既不是我们的,勉强藏匿起来,这辈子也不敢拿出来示人,且良心难安,不是吗?”
谢慎老泪纵横起来:“不错。我枉为人父,我口口声声交教导你们,为人要干净纯良,才能做好珐琅,可现在我却这样糊涂……”
“我知道了,您放心,我这就拿去还给傅家。”谢京福终于明白原来父亲藏了这样的私心,也因为此事曾经殚精竭虑地以图心安,最终还是难以逾越良心之谴。
他看到父亲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也深深理解父亲的心意。他告诉自己,要好好满足老人家的心愿,不再忤逆了。
他也没有想到,再次踏入傅家,竟然是由于谢家的过错。他反复演练了多次对这件事的说辞,一路忐忑不安的,一想到要面对伊杭的面,说出这些,还是有些难以启齿。他走进傅家,听到的是里边喧闹的人声,隐隐还有傅恒远的怒骂声和伊杭的哭声,他暗道一声:“不好。”便冲进了院子。
果然,院子里的花草被践踏成泥,水缸也被砸成了两瓣。傅恒远趴在屋檐下,凌乱的头发上到处是脏水,他捂着自己的右腿,低声呻吟着。而伊杭正朝那些人鞠躬:“请宽限几天吧!我一定想办法还上钱。”
为首的一个男子,看着伊杭吹弹可破的肌肤,一把抬起伊杭的下颚,嘿嘿笑道:“你这小模样倒是不错,要是你肯跟了我,我就免了你家的债,还给你娘出医药费,怎么样?”
伊杭怒意地挣脱了那男子的桎梏,朝他说:“如果你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那男子“喝”了一声:“还挺厉害,我看你能够厉害到什么时候?”
他说着,伸出手就拉扯伊杭,伊杭朝后退去,但是当她再抬头看到,谢京福已经拦住了那男子。
男子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子我混江湖也多年了,从来都是我当护花使者,今天怎么还来了插一杠子的?”
谢京福郑重其事的说:“如果你敢再动他们一根手指头,我就去公安局告你们,现在是法制社会,不是过去混江湖的旧社会了,难道你们以为国家的法制还真是说着玩的。”
那男子怒笑:“别拿那些公检法吓唬老子,老子不怕!”
此刻,他后边的几个人凑过来小声说:“大哥,我们只是来要债的,不是来要人命的。别忘了上次你在公安局签了保证书的,可不要因小失大了!”
男子思索了片刻,挥了挥手,指着傅恒远说:“好吧,我告诉你,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你如果再不换钱,我就烧了你家这宅子!”
傅恒远“哼”着:“你烧了这房子,我拿什么还债?”
男子不甘心地往外走,说道:“你自己想想,欠债不还,总是要有个说法。”他说完,示意自己的人离开。
傅恒远斜着眼睛看着这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才壮起胆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谢家小子,你又来了,我家可不欠你工钱,你来做什么?”
谢京福捏了捏裤兜里的盒子,心想这东西还是不能交给傅恒远,否则怕是一去不回,于是点头说:“我爹说时间不短了,让我过来问问,傅家还有什么活要做的?”
“还算你们有良心,哦呵……”傅恒远呻吟着,摸着自己的臀部,“如果你们谢家还记挂着我们傅家对你们的恩情,现在也该站出来偿还了,是不是要拿些钱出来先顶顶风声呢?”
谢京福不知道怎么回复这话,只好闷声不语。
“阿玛!”伊杭听了这话,心中悲愤,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到了现在你还说这样大言不惭的话,难道你真的想让我和额娘都无家可归吗?想让每一个和我们的傅家有关系的人都以你为耻吗?真是想把我们这个家最后一点儿脸面都丢尽吗?”
“你这丫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傅恒远歪着嘴,不乐意地说,“我现在是走到哪里都被人嫌,是不是你们也嫌弃我了?”
“阿玛?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和我额娘都被你给逼成什么样子了?我额娘她……都病得这样重了,你居然一点儿都不顾她,你到底长没长心啊?”
傅恒远似乎还沉浸在昨日的宿醉里,他眯着眼睛,说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还是钱有用,谁给我钱,让我管谁叫祖宗都成,我连自己的都保不住,哪里还有能力来保你们?对了,丫头,你最近生意不是做得风声水起,你挣的钱呢?还不拿出些孝敬你阿玛?”
这话说得无情无义,谢京福觉得自己都浑身颤抖了几下,他慌乱地看着伊杭的脸色越来越惨白,明显已经被自己父亲气得几乎晕厥,他忽然很想做些什么,便对傅恒远说:“您还是顾些情义吧?毕竟这是您的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傅恒远似乎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他翻过身子,轻哼一声,说道,“说起这事来,还是真得细细琢磨一下,当年你额娘也是和她那个表哥是订了亲的,两个人暧昧得很,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呢?不过是我胸襟大,不计较罢了!”
听着这话,伊杭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嘤嘤哭泣起来。
谢京福一看到伊杭伤心,就有些抑制不住,他的脸色变了,深深呼吸了一口,鼓起了勇气,想和这傅家主人理论一番。
“傅恒远,你好狠心!”谢京福看到门口站着那面色晦暗的侧福晋水莲,她扶着门框,一边喘息着,一边指着傅恒远说,“我跟了你这么多年,千难万难,千苦万苦,我都能受的,只是因为心里还牵挂着你对我的一份情意,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心思,我真是悔不该当初没听父母的话,才有了今天的报应,我活该!我该千刀万剐!但是,你不要侮辱我们的孩子,她是堂堂正正的满族格格,她骨子里都是高贵的气质,这是你用多少肮脏的语言都淹没不了的!傅恒远,我看透了你,从今天开始,我只有女儿,没有丈夫!”
她说完,又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很快就颓靡地倒了下去。伊杭大声喊着“额娘”,便冲了过去。谢京福也赶紧过去,搀扶起侧福晋。
只见侧福晋水莲的眼皮不停地煽动着,她孱弱地攥紧自己女儿的手,说:“孩子,去找你表舅去,离开这里,去杭州找你的外祖母,不然,怕是这个家要害死你!”
这话说完,她便垂下了手,闭上了眼睛,再无声息。伊杭看到母亲手中的帕子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忽然有种即将失去的恐惧感,她不由大声喊着:“额娘,你醒醒,我不要你死!不要!”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