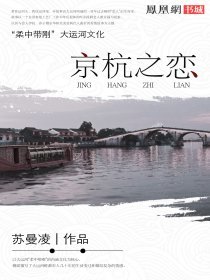第七章 同舟共济3
德胜门丝绸总店里,冯友源正高兴地送走了几个客人。忽然眼前一道异样的风景夺了眼球。只见一个身穿素衣的女子,脸色苍白,似乎刚刚经历了什么人间劫难一般。走的近了他心中惊呼了一声,原来那是傅伊杭,她的右臂上带了一个孝牌。
冯友源感觉自己的心莫名紧了一下,他正想说话,却看到库寿山朝傅伊杭走去。
“傅经理,您这是来清付上次欠的尾款吗?”
伊杭有些窘迫,只好低声敛眉:“库经理,我想再晚些支付那笔款子,因为我家母刚刚生病过世,家里用钱的地方多,所以想……”
“傅经理,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还有,那些货款都是公款,你这样是挪用公款,是犯法的。”库寿山的脸上没有笑容,对于伊杭所说的刚刚丧母之事,也没有半分恻隐之心。
“库经理,您误会了。我只是由于家里事情多,也只想提前预支两个月工资,并没有挪用公款。”
冯友源听到了这话,心中有些不安,他刚刚想把傅伊杭叫进来说些安慰的话,但是忽然有人进来汇报:“冯经理,杭州总厂发了电报来,说那些缫丝工和车间主任打起来了,还有我们上次送到上海的货,据说是法国客商订购的,那批货听说出了很多残次品,人家要退货,还要告我们不守信用,以次充好。”
冯友源听得眉头皱了起来:“好,我知道了,我这就收拾行李回杭州。”
他摇了摇头,这次不仅仅要立刻回杭州,恐怕还要到上海出一趟差,这是国际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丝绸厂的信誉。他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却看不到傅伊杭的身影了。
只见库寿山连忙近前说:“冯经理,你有什么事要吩咐?”
冯友源说:“厂里有些急事,需要我立刻要回杭州一趟,你要好好打理这边的事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拿捏的,要随时向我汇报。对了,还有,那位傅经理如果遇到什么难事,你要多体谅,多帮助,不要为难。咦,她怎么忽然走了?”
库寿山答道:“傅经理说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就匆忙走了。”
“她没说有什么事吗?看她的脸色可是不太好。既然已经是咱们自己人,人家有什么困难,就要帮忙解决,不要为难。虽然我们也有规定,但是法外容情,也不是不可以的。”
库寿山连连称是:“知道了。傅经理这次来只是问上次订购的货来了吗?我们的货都在路上,明后天就差不多可以入库了。傅经理好像有什么忌讳,我也不方便过问太多,她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说完,他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冯友源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时间非常紧急,不能耽误了,只好下次来北京再找傅伊杭谈一谈。他还记得,当时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让她拿出设计图来。他以为她只是一时图个新鲜,只要日子久了,就不会再坚持的。没想到,只不过一个多礼拜,那个姑娘就拿着自己的设计图来,她指着那蓝色的杏花与水红色的点染,笑着说:“这个设计叫‘京杭之恋’。”
京杭之恋?冯友源当时并不明白这姑娘要做什么,只听姑娘说:“这蓝色是冷色纯净的色彩,是一个心中有责任又感性的男子,而这水红色为暖色,则是一个日日盼郎归心的女子,两种色调搭配,人间冷暖自然就知道了。一年四季都可用这丝绸做衣服。”冯友源惊喜地看到那姑娘露出一排珍珠贝一般的牙齿,微微笑了。
他内心激情澎湃,似乎发现了一个无价珍宝。当下丝绸厂的外销并不太好,国家主张多创汇增效,但是多年来,传统纹饰使一些国外客商产生了审美疲劳,因此销量大大下降。他发现,主要是丝绸厂缺少设计人员,而眼前这个姑娘画的一手好丹青,还极其富有创作灵性,是丝绸厂急需的设计人才。只不过,由于她的双亲尚在,离开北京城并不便利,只好答应她先做丝绸厂的合作分销经理。这次回去,也要把这款设计提交到厂部,如果得到通过,就可以大批量生产了。
他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叮嘱了库寿山几句,就匆匆离开了。
伊杭迈着软绵绵的步子,独自一个人慢慢回到自己的丝绸店。店里并没有之前的热闹繁华,只有两个店员正在用指甲刀修复指甲。
伊杭知道天气凉了,自己该进些厚重的面料,否则就失去了更多的客户。但是每次去总店调货,都是无功而返。那个叫库寿山的销售经理并不喜欢自己,每次去说话都阴阳怪气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
她并没有责怪店员无所事事,是自己这个经理当得不合格。看来自己果然没有做生意的天赋。她只好叮嘱了店员几句,自己便先想着回家看看。
她回到家,想找到谢京福上次送来的鸽血红宝石,本想将这几样东西留作纪念,不再变卖的。眼下季节丝绸生意凋零,资金周转不灵,她想和几家裁缝店合作,做出成衣展示,这样的效果会更好。现在一时半会儿从总店调不来合适的面料,只有自己先垫付资金,看外贸有什么进口面料先应付一下。她想了想,还是决定变卖三颗红宝石。但是,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她把米桶都翻出来找了好几遍,几乎要一粒一粒去数那些大米,米并不太多,但是红宝石确实不见了。
她疯狂一般地冲出来,到处寻找自己的父亲,果然看到父亲在前院晒着太阳,一边喝着一边唱着,似乎做了什么得意的事。
“阿玛?你还我红宝石,你又把它们拿到哪里去了?”
傅恒远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自己女儿气急败坏地朝自己喊着,不禁又不高兴了:“什么宝石?你有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拿了?这还是什么格格嘛,对自己的阿玛还这样大呼小叫的。”
“阿玛……您这是要逼死您的女儿吗?”伊杭简直被这个没落的满族纨绔子弟、自己的亲生父亲,给逼得想要走向绝路了。她真不愿意相信,自己身上居然流着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的血液。
“看看,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一个大活人,不是好好呆在这里吗?谁逼你的?”
“您已经逼死了我的额娘,难道你还要逼死我吗?如果您非要我死,那我现在就死给您看!”伊杭气得已经不知道自己朝哪里走了,她只知道,自己家前院,还有一口古井,她径直朝那里走了去。
但是,她没走几步,就被一个散发着茉莉花香的身体给拦住了。她定睛一看,原来是凌云。她挎着一只蓝色的牛皮包,似乎也考虑了傅家刚刚办完丧事,特意穿着一身素淡的连衣裙。
“我说伊杭格格,你这是何苦?这样的爹,还受着他做什么?不如自己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一劳永逸,让你这个没脸没皮的爹自己混日子吧!眼不见为净!”
伊杭被凌云这几句话给塞得清醒了几分,她警觉地看着这个女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她的来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倒是傅恒远有些不乐意了,他哼着,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凌云,说道:“我说这是谁呢?冷锅里冒热气,怎么想我这来了?不嫌我家门庭简陋,污了您的眼了?”
凌云一张抹得妖红的嘴唇顿时飞快地动了起来,她也随着傅恒远的问话笑了起来:“我这不是替咱家格格着想,姑娘大了,该找了好人家的,这个也是正事,您这个做爹的也该为自己的女儿操点心了,整日里醉生梦死的,还有什么意思?”
傅恒远听着凌云这绵里藏针的说法有些恼怒:“别人醉不醉、死不死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有空还是管管自己,别成天没事找事,咸吃萝卜淡操心。”
伊杭也连忙接着说:“我母亲刚刚殁了,我还要给母亲守孝。再说我年纪还小,不想嫁人。谢谢凌云阿姨的好意。”
“哎呦,真的不想听听,对方可是整个北京城都数的着的大户人家呢!”
傅恒远听到“大户”这两个字,口气明显松了起来,他拿起一只掏耳勺边掏耳朵边说:“说来听听也成。”
“这个人说起来你们也认识,就是西城北面大名鼎鼎的古董商高俊山,家里可是还有很多房产和金银财宝的。半年前那夫人因病过世,所以想找个聪明伶俐识大体、会持家的姑娘做填房。”
“什么?”傅恒远伸出左手长得细长指甲的小拇指,不耐烦的掏了一下耳屎,说,“那个老家伙和我差不多年纪,难道你想让我卖闺女,那种不仁不义的事情,我傅恒远可做不出来。”
“这是说的哪的话?您看看,这不是冤枉我了吗?”凌云凑进傅恒远的面前,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贝齿,“我这可是为了傅家好。实话实说,傅家还真是亏待了长子,虽然人不在,但是这家产可是不能没有人家的份,您说说,您这心都偏哪里去了?”
冯友源感觉自己的心莫名紧了一下,他正想说话,却看到库寿山朝傅伊杭走去。
“傅经理,您这是来清付上次欠的尾款吗?”
伊杭有些窘迫,只好低声敛眉:“库经理,我想再晚些支付那笔款子,因为我家母刚刚生病过世,家里用钱的地方多,所以想……”
“傅经理,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还有,那些货款都是公款,你这样是挪用公款,是犯法的。”库寿山的脸上没有笑容,对于伊杭所说的刚刚丧母之事,也没有半分恻隐之心。
“库经理,您误会了。我只是由于家里事情多,也只想提前预支两个月工资,并没有挪用公款。”
冯友源听到了这话,心中有些不安,他刚刚想把傅伊杭叫进来说些安慰的话,但是忽然有人进来汇报:“冯经理,杭州总厂发了电报来,说那些缫丝工和车间主任打起来了,还有我们上次送到上海的货,据说是法国客商订购的,那批货听说出了很多残次品,人家要退货,还要告我们不守信用,以次充好。”
冯友源听得眉头皱了起来:“好,我知道了,我这就收拾行李回杭州。”
他摇了摇头,这次不仅仅要立刻回杭州,恐怕还要到上海出一趟差,这是国际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丝绸厂的信誉。他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却看不到傅伊杭的身影了。
只见库寿山连忙近前说:“冯经理,你有什么事要吩咐?”
冯友源说:“厂里有些急事,需要我立刻要回杭州一趟,你要好好打理这边的事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拿捏的,要随时向我汇报。对了,还有,那位傅经理如果遇到什么难事,你要多体谅,多帮助,不要为难。咦,她怎么忽然走了?”
库寿山答道:“傅经理说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就匆忙走了。”
“她没说有什么事吗?看她的脸色可是不太好。既然已经是咱们自己人,人家有什么困难,就要帮忙解决,不要为难。虽然我们也有规定,但是法外容情,也不是不可以的。”
库寿山连连称是:“知道了。傅经理这次来只是问上次订购的货来了吗?我们的货都在路上,明后天就差不多可以入库了。傅经理好像有什么忌讳,我也不方便过问太多,她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说完,他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冯友源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时间非常紧急,不能耽误了,只好下次来北京再找傅伊杭谈一谈。他还记得,当时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让她拿出设计图来。他以为她只是一时图个新鲜,只要日子久了,就不会再坚持的。没想到,只不过一个多礼拜,那个姑娘就拿着自己的设计图来,她指着那蓝色的杏花与水红色的点染,笑着说:“这个设计叫‘京杭之恋’。”
京杭之恋?冯友源当时并不明白这姑娘要做什么,只听姑娘说:“这蓝色是冷色纯净的色彩,是一个心中有责任又感性的男子,而这水红色为暖色,则是一个日日盼郎归心的女子,两种色调搭配,人间冷暖自然就知道了。一年四季都可用这丝绸做衣服。”冯友源惊喜地看到那姑娘露出一排珍珠贝一般的牙齿,微微笑了。
他内心激情澎湃,似乎发现了一个无价珍宝。当下丝绸厂的外销并不太好,国家主张多创汇增效,但是多年来,传统纹饰使一些国外客商产生了审美疲劳,因此销量大大下降。他发现,主要是丝绸厂缺少设计人员,而眼前这个姑娘画的一手好丹青,还极其富有创作灵性,是丝绸厂急需的设计人才。只不过,由于她的双亲尚在,离开北京城并不便利,只好答应她先做丝绸厂的合作分销经理。这次回去,也要把这款设计提交到厂部,如果得到通过,就可以大批量生产了。
他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叮嘱了库寿山几句,就匆匆离开了。
伊杭迈着软绵绵的步子,独自一个人慢慢回到自己的丝绸店。店里并没有之前的热闹繁华,只有两个店员正在用指甲刀修复指甲。
伊杭知道天气凉了,自己该进些厚重的面料,否则就失去了更多的客户。但是每次去总店调货,都是无功而返。那个叫库寿山的销售经理并不喜欢自己,每次去说话都阴阳怪气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
她并没有责怪店员无所事事,是自己这个经理当得不合格。看来自己果然没有做生意的天赋。她只好叮嘱了店员几句,自己便先想着回家看看。
她回到家,想找到谢京福上次送来的鸽血红宝石,本想将这几样东西留作纪念,不再变卖的。眼下季节丝绸生意凋零,资金周转不灵,她想和几家裁缝店合作,做出成衣展示,这样的效果会更好。现在一时半会儿从总店调不来合适的面料,只有自己先垫付资金,看外贸有什么进口面料先应付一下。她想了想,还是决定变卖三颗红宝石。但是,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她把米桶都翻出来找了好几遍,几乎要一粒一粒去数那些大米,米并不太多,但是红宝石确实不见了。
她疯狂一般地冲出来,到处寻找自己的父亲,果然看到父亲在前院晒着太阳,一边喝着一边唱着,似乎做了什么得意的事。
“阿玛?你还我红宝石,你又把它们拿到哪里去了?”
傅恒远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自己女儿气急败坏地朝自己喊着,不禁又不高兴了:“什么宝石?你有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拿了?这还是什么格格嘛,对自己的阿玛还这样大呼小叫的。”
“阿玛……您这是要逼死您的女儿吗?”伊杭简直被这个没落的满族纨绔子弟、自己的亲生父亲,给逼得想要走向绝路了。她真不愿意相信,自己身上居然流着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的血液。
“看看,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一个大活人,不是好好呆在这里吗?谁逼你的?”
“您已经逼死了我的额娘,难道你还要逼死我吗?如果您非要我死,那我现在就死给您看!”伊杭气得已经不知道自己朝哪里走了,她只知道,自己家前院,还有一口古井,她径直朝那里走了去。
但是,她没走几步,就被一个散发着茉莉花香的身体给拦住了。她定睛一看,原来是凌云。她挎着一只蓝色的牛皮包,似乎也考虑了傅家刚刚办完丧事,特意穿着一身素淡的连衣裙。
“我说伊杭格格,你这是何苦?这样的爹,还受着他做什么?不如自己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一劳永逸,让你这个没脸没皮的爹自己混日子吧!眼不见为净!”
伊杭被凌云这几句话给塞得清醒了几分,她警觉地看着这个女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她的来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倒是傅恒远有些不乐意了,他哼着,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凌云,说道:“我说这是谁呢?冷锅里冒热气,怎么想我这来了?不嫌我家门庭简陋,污了您的眼了?”
凌云一张抹得妖红的嘴唇顿时飞快地动了起来,她也随着傅恒远的问话笑了起来:“我这不是替咱家格格着想,姑娘大了,该找了好人家的,这个也是正事,您这个做爹的也该为自己的女儿操点心了,整日里醉生梦死的,还有什么意思?”
傅恒远听着凌云这绵里藏针的说法有些恼怒:“别人醉不醉、死不死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有空还是管管自己,别成天没事找事,咸吃萝卜淡操心。”
伊杭也连忙接着说:“我母亲刚刚殁了,我还要给母亲守孝。再说我年纪还小,不想嫁人。谢谢凌云阿姨的好意。”
“哎呦,真的不想听听,对方可是整个北京城都数的着的大户人家呢!”
傅恒远听到“大户”这两个字,口气明显松了起来,他拿起一只掏耳勺边掏耳朵边说:“说来听听也成。”
“这个人说起来你们也认识,就是西城北面大名鼎鼎的古董商高俊山,家里可是还有很多房产和金银财宝的。半年前那夫人因病过世,所以想找个聪明伶俐识大体、会持家的姑娘做填房。”
“什么?”傅恒远伸出左手长得细长指甲的小拇指,不耐烦的掏了一下耳屎,说,“那个老家伙和我差不多年纪,难道你想让我卖闺女,那种不仁不义的事情,我傅恒远可做不出来。”
“这是说的哪的话?您看看,这不是冤枉我了吗?”凌云凑进傅恒远的面前,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贝齿,“我这可是为了傅家好。实话实说,傅家还真是亏待了长子,虽然人不在,但是这家产可是不能没有人家的份,您说说,您这心都偏哪里去了?”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