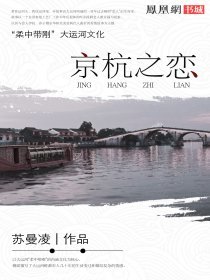第八章 一枕黄粱2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满地都是银杏叶,路人的脖子里多了一条御寒的围巾,也有马车拉着过冬的煤往市里去。这才让谢京福想起来,该准备过冬的煤了,否则遇到寒流就会有些手忙脚乱。谢京福一边将自己家的煤都拉回来屯到院子里,一边想起,伊杭家里肯定是冷冰冰的,该去看看,帮她拉些煤回来。
但是,谢京福想了想,拉煤不一定今天就可办成,还是先换身衣服再去。他换上了藏在柜子里的一套新衣服,洗干净了脸,又打开父亲的老榆木脚柜,翻出里边珍藏多年的两瓶刘伶醉,提了两盒桃酥,还有,就是将那一直没有送出去的花青也带上,一路出门,直奔伊杭在东安市场的店面。
他感觉自己脚下生风,仿佛被施了魔法,注入了无穷的力量。他不期待这一次自己一定会心想事成,但是他为自己终于有勇气可以向喜欢的姑娘吐露心声而开心。自从看到伊杭可以放下身段,去开店经营事业,看到伊杭可以和人流中的所有人一样,用最真实的状态活着,心中才渐渐笃定,他感激这个国家的建立,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别都消除了,让他和伊杭没有了主仆之分,将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也许,这一切都是两个人的缘分。
但是,他到了伊杭的丝绸店前,发现大门紧闭,有一群人围着看热闹,外边有几个消防兵正忙着。而店铺里里外外早就没有了原来的高雅格调,而是被烧得黑漆漆一片。
他询问路人,发生了什么。
有人告诉他,听说这里的店主得罪了黑社会,这里昨天被一群人给烧了,可惜了,里边那些高贵的杭州丝绸都化成了灰烬。现在消防兵正在排查,看还有没有别的隐患。
谢京福顿时觉得心如流星一般坠落,他没有看到伊杭的身影,忽然觉得心中恐慌起来,意识到有什么不良的事情发生。他顾不得手中的酒瓶子叮当作响,一路狂奔,直接奔到傅家。
果然,傅家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傅家的大门口贴满了红彤彤的“喜”字,也是一个双“喜”,和之前他给那家嫁姑娘的人家设计的“喜”字居然一模一样。他看着外边有人探头探脑、窃窃私语,不禁急切问道:“这里有什么事吗?”
有人翻了一个白眼,摇头说:“是喜事,也是悲惨的事。”
“什么?”
那人看着谢京福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不禁好笑:“你是这家的亲戚吗?你来晚了,这家的姑娘刚刚嫁到西城高家。唉,这家听说还是以前满清的贵族‘格格’,这是让自己的亲爹给坑了,简直是匪夷所思。”
谢京福听得有些着急,扯着那人的胳膊喊:“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不太清楚,只是听说那个不着调的爹把家里仅有的三颗红宝石给偷去赌了,结果不但血本无归,还欠了一笔巨额债务,结果被人家把店铺给烧了……这老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到处求人,结果无人问津,于是喝的酩酊大醉,一下子摔倒了石头上,听说成了植物人,这样傅家是揭不开锅了,于是想着卖房子吧,没想到又被一个远方亲戚给套了,房子也成了人家的,姑娘走投无路,只好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
“啪……”谢京福没等听完,就把手中的酒瓶子和桃酥都扔到了地上,任凭那带着沧桑的酒香淡淡飘在空气中。
他急忙问:“高家在哪里?”
“就是顺着这条街走到尽头,再朝右拐,然后朝左手拐进去,看到一个大四合院,门前有两株大株国槐。高家可是有钱人,那门面阔气得很,去了就看的到。新娘子刚给接走了一个多小时,估计这会儿正大宴宾客呢!”
“谢谢。”
“可惜了这样好的姑娘,老牛吃嫩草,一朵鲜花插牛粪上……”
谢京福听到这话时,人已经离开了七步以外。他撒开腿,拼命地狂奔起来,一路险些撞到人。他按照那人说的,气喘吁吁地跑了两三条街,果然看到不远处一个大四合院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到处人来来往往的人,地上也撒满了五颜六色的喜花。那宽阔的大门两侧悬挂着两只红红的灯笼,红色光晕中隐隐约约看到写着“高宅”两个字。他没考虑什么,径直就冲了进去。
高家管事的人,看一眼谢京福穿得崭新体面,以为是来参加喜宴的亲戚,便指引领着谢京福和其他人一起往会客厅而去。谢京福悄悄离开那群人,自己独自一个人从侧面的小门穿过,往后院而去。这院子果真是宽敞亮堂,几株大桑树下边,是一个爬满了葫芦的架子,架子下边有一张石桌,石桌旁边正坐着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姑娘,低头垂泪不语。
谢京福屏住呼吸,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一直朝那个在心头萦绕了千遍万遍的窈窕身影走去。那是他的伊杭,不用再问,只看一眼那瘦弱的肩头和乌黑的秀发,就知道那一定是她。
他心头藏了千言万语,却从来没有机会倾诉。那她本是他放到心里,想终生相伴的女子。世间万事,竟真的是百转千回,当他终于可以有勇气面对她的时候,她却已成他人妇。他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便再一次面临失去。
谢京福心头剧痛,这是上天对他犹而不决的惩罚?他每走一步,都觉得愈发沉重一层,直到走到她背后,鼓起全部的勇气,轻轻喊了一声:“伊杭。”
这一声竟然让眼前的姑娘颤抖了一下,她骤然转头,惊喜地喊了一声:“谢大哥,怎么是你?”
谢京福抿着嘴,没有笑,只说了一句:“伊杭,和我走,离开这里。”
伊杭听了谢京福的话,两滴泪就那样无声地滑落下来,让谢京福心中更加觉得恐慌。他宁愿眼前的伊杭和以前一样抱着自己的肩头大声哭泣,宁愿看到她忽逢暴风骤雨时带着几分天真与纯洁的躲避,而不是现在这样哀绝。短短几天,她苍白的脸上多了几分世故与从容,这种从容让人觉得疏离。
“谢大哥,没有想到在我结婚的时候,只有你来送我。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就告诉你,我需要高家的钱,我现在只需要钱,只有钱才能救我。”
谢京福心中犹豫着,很想大声说出来:“我不想做你的亲人,只想做你的爱人。”但是他还是哽咽一声,将这句话咽了下去。他并没有能力助她渡过难关,并没有多余的钱财可以给她的父亲交医药费,他是个对她可有可无的人。
“只要我们两个人努力,一切都可以过去。我可以帮你,伊杭。”
“不,来不及了,谢大哥,我也不能再拖累你了,你们谢家对我们傅家已经尽了全力,我会报答你们的。”
“我不要你报答,我只是要你清醒一下,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这样牺牲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可值得?”
伊杭点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小时候,亲眼看到母亲以泪洗面,一辈子郁郁寡欢,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自己活出一份天地来,不要再和母亲一样,为了一个不值得自己爱的人,背井离乡,却不得饱满。高家有财力有地位,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伊杭,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谢京福听到隔壁的院子里熙熙攘攘的声音,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和伊杭说清楚,不希望她将来会为现在的选择而后悔。
但是他听到伊杭这样说:“谢大哥,我很清醒,我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不要尊严的爱钱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我是和我父亲一样的落魄贵族。我曾经也想靠自己的能力撑出一片天地来,但是我把这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所以我败得一塌糊涂。我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婚姻,就不会后悔,因为这也是我该经历的人生吧!我愿意接受这种人生带给我的所有快乐的和痛苦的感受。谢大哥,我知道你会懂得我的选择。”
谢京福看到伊杭的眼神里是一股自己从来都不曾看到过的光彩,那光彩带着飞蛾扑火却刹那间辉煌炫丽的决绝,将自己想说的话都堵了回去。
于是,他伸出手,想拉住她,甚至想将她裹挟在自己怀中,抱着她,冲出眼前这个藩篱中,让她更加鲜活地活着。但是伊杭对自己是拒绝的,他看的出来,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人,是可以娶妻生子的。
他顿时豁悟,明白自己与伊杭的差距了,就是这份不同的思维与格局,就是这种明明是逆境也可以充满期待地看未来。他想的,只是怎么挣脱眼前这苦难,却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怎样用最有效的方式解决所有的困难。
伊杭不会知道,她赌的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对于谢京福来说,输的也是一辈子的幸福。
他只好将自己的手放了下来,说:“你真的可以?”
伊杭点点头:“你放心,谢大哥。今天我很满足,因为我父亲自己的不检点,将整个家族的名誉毁于一旦,我的叔伯婶娘们和所有的亲戚都拒绝再和我家沾上关系,我没有人送嫁,只有你谢大哥,还愿意来到我身边,所以我才说你是我的亲人。”
“我……”谢京福蓦地发现,伊杭并没有再称呼自己的父亲为“阿玛”,她的这种变化让谢京福有些惶然。
“高俊山虽然是个算计了一辈子的商人,但是他毕竟没有什么劣迹,对自己的亲人也还尽心,也体恤我的难处,帮助我将所有的事儿一一打理完毕,所以我也相信,他是个成全我的人。”
正说着,忽然看到一个头发有些发白,身穿新郎服饰的中年男子一边喊着“伊杭”,一边走了过来。
“这是哪一位?伊杭,给我介绍一下。”
伊杭抹了一眼脸上了残泪,换了一副笑容,指着谢京福说:“这是我的丈夫高俊山,这是一直帮扶我傅家的兄长谢大哥,我的至亲,是我的娘家人。如果你要是欺负我,他就会来给我主持公道。”
高俊山听了这话,一顿“哈哈”大笑:“伊杭,你又开玩笑了!既然是你的娘家人,可不能当着娘家人,开这种玩笑,我哪里舍得欺负你,心疼你还来不及。”
谢京福倒是有些尴尬了,他喃喃地说:“不敢。”
“好,时间不早了,宾客们已经开始进餐了,我们也去敬个酒,请你娘家兄长也进去参加喜宴。”
伊杭点头,朝谢京福示意。谢京福只好跟着两个人,被引领着,坐在了主宾的位置上。
他知道,自己这一场难以遏制的相思再次成空。第一次,他在别人的敬意中,享受着伊杭给予自己的尊重。他喝了几大口酒,酒带着难以掩饰的烈性冲击得他四肢百骸都热了起来。他就这样,看着自己爱的女人和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男子拜堂成亲,进入洞房。
他终究是看不下去这种场面,虚与蛇委了一会儿,便借故离去。他该走了,这里已经容纳不了自己。以前给傅家做珐琅修珐琅,还有机会看一眼她。但是,今后,她的身边只会站立那个年龄可以做她父亲的男子,他牵着她的手,和别人到处介绍自己年轻貌美又有贵族身份的妻子,成就自己的得意人生。
每一次来见她,都是带着发自肺腑的欢欣。但每一次离去,都带着撕心裂肺的疼痛。也许,这就是他与她的缘。伊杭已经不是那个天真纯洁的少女了,她想要的,自己给不了她。谢京福就这样茫然空洞地一步一步走了回来。
家里,和以往一样,许是父亲已经睡了,四周都寂静得很。但是当他踏入内堂的瞬间,迎面就被一个冲过来的人给挡住,来不及细想,他的脸就被对方狠狠挠了一下。
他忍着火辣辣的疼痛,定神看去,原来是哭得眼睛都肿得像桃子的兰姨,兰姨并没有因为这一下而解气,而是疯了一般,边哭边骂边再次朝自己捶了过来:“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管你们吃管你们喝这么多年,都换不来一点儿好。现在又是你这小子害死我家慧珍,如果慧珍有什么事情,我就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不放过你们谢家!”
谢京福瞬间清醒了,他看到父亲依旧站在里边,颤巍巍地跺着拐杖,说:“打,使劲打,他兰姨,你放心,就是你打死了他,我谢慎也决不会说一个‘不’字,他是罪有应得,他活该!”
谢京福被这情景惊得魂飞魄散,他知道定然是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于是,他抓住兰姨的手说:“兰姨,发生什么了?请告诉我,该我负责的我一定负责。”
但是,谢京福想了想,拉煤不一定今天就可办成,还是先换身衣服再去。他换上了藏在柜子里的一套新衣服,洗干净了脸,又打开父亲的老榆木脚柜,翻出里边珍藏多年的两瓶刘伶醉,提了两盒桃酥,还有,就是将那一直没有送出去的花青也带上,一路出门,直奔伊杭在东安市场的店面。
他感觉自己脚下生风,仿佛被施了魔法,注入了无穷的力量。他不期待这一次自己一定会心想事成,但是他为自己终于有勇气可以向喜欢的姑娘吐露心声而开心。自从看到伊杭可以放下身段,去开店经营事业,看到伊杭可以和人流中的所有人一样,用最真实的状态活着,心中才渐渐笃定,他感激这个国家的建立,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别都消除了,让他和伊杭没有了主仆之分,将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也许,这一切都是两个人的缘分。
但是,他到了伊杭的丝绸店前,发现大门紧闭,有一群人围着看热闹,外边有几个消防兵正忙着。而店铺里里外外早就没有了原来的高雅格调,而是被烧得黑漆漆一片。
他询问路人,发生了什么。
有人告诉他,听说这里的店主得罪了黑社会,这里昨天被一群人给烧了,可惜了,里边那些高贵的杭州丝绸都化成了灰烬。现在消防兵正在排查,看还有没有别的隐患。
谢京福顿时觉得心如流星一般坠落,他没有看到伊杭的身影,忽然觉得心中恐慌起来,意识到有什么不良的事情发生。他顾不得手中的酒瓶子叮当作响,一路狂奔,直接奔到傅家。
果然,傅家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傅家的大门口贴满了红彤彤的“喜”字,也是一个双“喜”,和之前他给那家嫁姑娘的人家设计的“喜”字居然一模一样。他看着外边有人探头探脑、窃窃私语,不禁急切问道:“这里有什么事吗?”
有人翻了一个白眼,摇头说:“是喜事,也是悲惨的事。”
“什么?”
那人看着谢京福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不禁好笑:“你是这家的亲戚吗?你来晚了,这家的姑娘刚刚嫁到西城高家。唉,这家听说还是以前满清的贵族‘格格’,这是让自己的亲爹给坑了,简直是匪夷所思。”
谢京福听得有些着急,扯着那人的胳膊喊:“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不太清楚,只是听说那个不着调的爹把家里仅有的三颗红宝石给偷去赌了,结果不但血本无归,还欠了一笔巨额债务,结果被人家把店铺给烧了……这老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到处求人,结果无人问津,于是喝的酩酊大醉,一下子摔倒了石头上,听说成了植物人,这样傅家是揭不开锅了,于是想着卖房子吧,没想到又被一个远方亲戚给套了,房子也成了人家的,姑娘走投无路,只好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
“啪……”谢京福没等听完,就把手中的酒瓶子和桃酥都扔到了地上,任凭那带着沧桑的酒香淡淡飘在空气中。
他急忙问:“高家在哪里?”
“就是顺着这条街走到尽头,再朝右拐,然后朝左手拐进去,看到一个大四合院,门前有两株大株国槐。高家可是有钱人,那门面阔气得很,去了就看的到。新娘子刚给接走了一个多小时,估计这会儿正大宴宾客呢!”
“谢谢。”
“可惜了这样好的姑娘,老牛吃嫩草,一朵鲜花插牛粪上……”
谢京福听到这话时,人已经离开了七步以外。他撒开腿,拼命地狂奔起来,一路险些撞到人。他按照那人说的,气喘吁吁地跑了两三条街,果然看到不远处一个大四合院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到处人来来往往的人,地上也撒满了五颜六色的喜花。那宽阔的大门两侧悬挂着两只红红的灯笼,红色光晕中隐隐约约看到写着“高宅”两个字。他没考虑什么,径直就冲了进去。
高家管事的人,看一眼谢京福穿得崭新体面,以为是来参加喜宴的亲戚,便指引领着谢京福和其他人一起往会客厅而去。谢京福悄悄离开那群人,自己独自一个人从侧面的小门穿过,往后院而去。这院子果真是宽敞亮堂,几株大桑树下边,是一个爬满了葫芦的架子,架子下边有一张石桌,石桌旁边正坐着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姑娘,低头垂泪不语。
谢京福屏住呼吸,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一直朝那个在心头萦绕了千遍万遍的窈窕身影走去。那是他的伊杭,不用再问,只看一眼那瘦弱的肩头和乌黑的秀发,就知道那一定是她。
他心头藏了千言万语,却从来没有机会倾诉。那她本是他放到心里,想终生相伴的女子。世间万事,竟真的是百转千回,当他终于可以有勇气面对她的时候,她却已成他人妇。他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便再一次面临失去。
谢京福心头剧痛,这是上天对他犹而不决的惩罚?他每走一步,都觉得愈发沉重一层,直到走到她背后,鼓起全部的勇气,轻轻喊了一声:“伊杭。”
这一声竟然让眼前的姑娘颤抖了一下,她骤然转头,惊喜地喊了一声:“谢大哥,怎么是你?”
谢京福抿着嘴,没有笑,只说了一句:“伊杭,和我走,离开这里。”
伊杭听了谢京福的话,两滴泪就那样无声地滑落下来,让谢京福心中更加觉得恐慌。他宁愿眼前的伊杭和以前一样抱着自己的肩头大声哭泣,宁愿看到她忽逢暴风骤雨时带着几分天真与纯洁的躲避,而不是现在这样哀绝。短短几天,她苍白的脸上多了几分世故与从容,这种从容让人觉得疏离。
“谢大哥,没有想到在我结婚的时候,只有你来送我。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就告诉你,我需要高家的钱,我现在只需要钱,只有钱才能救我。”
谢京福心中犹豫着,很想大声说出来:“我不想做你的亲人,只想做你的爱人。”但是他还是哽咽一声,将这句话咽了下去。他并没有能力助她渡过难关,并没有多余的钱财可以给她的父亲交医药费,他是个对她可有可无的人。
“只要我们两个人努力,一切都可以过去。我可以帮你,伊杭。”
“不,来不及了,谢大哥,我也不能再拖累你了,你们谢家对我们傅家已经尽了全力,我会报答你们的。”
“我不要你报答,我只是要你清醒一下,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这样牺牲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可值得?”
伊杭点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小时候,亲眼看到母亲以泪洗面,一辈子郁郁寡欢,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自己活出一份天地来,不要再和母亲一样,为了一个不值得自己爱的人,背井离乡,却不得饱满。高家有财力有地位,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伊杭,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谢京福听到隔壁的院子里熙熙攘攘的声音,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和伊杭说清楚,不希望她将来会为现在的选择而后悔。
但是他听到伊杭这样说:“谢大哥,我很清醒,我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不要尊严的爱钱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我是和我父亲一样的落魄贵族。我曾经也想靠自己的能力撑出一片天地来,但是我把这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所以我败得一塌糊涂。我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婚姻,就不会后悔,因为这也是我该经历的人生吧!我愿意接受这种人生带给我的所有快乐的和痛苦的感受。谢大哥,我知道你会懂得我的选择。”
谢京福看到伊杭的眼神里是一股自己从来都不曾看到过的光彩,那光彩带着飞蛾扑火却刹那间辉煌炫丽的决绝,将自己想说的话都堵了回去。
于是,他伸出手,想拉住她,甚至想将她裹挟在自己怀中,抱着她,冲出眼前这个藩篱中,让她更加鲜活地活着。但是伊杭对自己是拒绝的,他看的出来,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人,是可以娶妻生子的。
他顿时豁悟,明白自己与伊杭的差距了,就是这份不同的思维与格局,就是这种明明是逆境也可以充满期待地看未来。他想的,只是怎么挣脱眼前这苦难,却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怎样用最有效的方式解决所有的困难。
伊杭不会知道,她赌的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对于谢京福来说,输的也是一辈子的幸福。
他只好将自己的手放了下来,说:“你真的可以?”
伊杭点点头:“你放心,谢大哥。今天我很满足,因为我父亲自己的不检点,将整个家族的名誉毁于一旦,我的叔伯婶娘们和所有的亲戚都拒绝再和我家沾上关系,我没有人送嫁,只有你谢大哥,还愿意来到我身边,所以我才说你是我的亲人。”
“我……”谢京福蓦地发现,伊杭并没有再称呼自己的父亲为“阿玛”,她的这种变化让谢京福有些惶然。
“高俊山虽然是个算计了一辈子的商人,但是他毕竟没有什么劣迹,对自己的亲人也还尽心,也体恤我的难处,帮助我将所有的事儿一一打理完毕,所以我也相信,他是个成全我的人。”
正说着,忽然看到一个头发有些发白,身穿新郎服饰的中年男子一边喊着“伊杭”,一边走了过来。
“这是哪一位?伊杭,给我介绍一下。”
伊杭抹了一眼脸上了残泪,换了一副笑容,指着谢京福说:“这是我的丈夫高俊山,这是一直帮扶我傅家的兄长谢大哥,我的至亲,是我的娘家人。如果你要是欺负我,他就会来给我主持公道。”
高俊山听了这话,一顿“哈哈”大笑:“伊杭,你又开玩笑了!既然是你的娘家人,可不能当着娘家人,开这种玩笑,我哪里舍得欺负你,心疼你还来不及。”
谢京福倒是有些尴尬了,他喃喃地说:“不敢。”
“好,时间不早了,宾客们已经开始进餐了,我们也去敬个酒,请你娘家兄长也进去参加喜宴。”
伊杭点头,朝谢京福示意。谢京福只好跟着两个人,被引领着,坐在了主宾的位置上。
他知道,自己这一场难以遏制的相思再次成空。第一次,他在别人的敬意中,享受着伊杭给予自己的尊重。他喝了几大口酒,酒带着难以掩饰的烈性冲击得他四肢百骸都热了起来。他就这样,看着自己爱的女人和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男子拜堂成亲,进入洞房。
他终究是看不下去这种场面,虚与蛇委了一会儿,便借故离去。他该走了,这里已经容纳不了自己。以前给傅家做珐琅修珐琅,还有机会看一眼她。但是,今后,她的身边只会站立那个年龄可以做她父亲的男子,他牵着她的手,和别人到处介绍自己年轻貌美又有贵族身份的妻子,成就自己的得意人生。
每一次来见她,都是带着发自肺腑的欢欣。但每一次离去,都带着撕心裂肺的疼痛。也许,这就是他与她的缘。伊杭已经不是那个天真纯洁的少女了,她想要的,自己给不了她。谢京福就这样茫然空洞地一步一步走了回来。
家里,和以往一样,许是父亲已经睡了,四周都寂静得很。但是当他踏入内堂的瞬间,迎面就被一个冲过来的人给挡住,来不及细想,他的脸就被对方狠狠挠了一下。
他忍着火辣辣的疼痛,定神看去,原来是哭得眼睛都肿得像桃子的兰姨,兰姨并没有因为这一下而解气,而是疯了一般,边哭边骂边再次朝自己捶了过来:“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管你们吃管你们喝这么多年,都换不来一点儿好。现在又是你这小子害死我家慧珍,如果慧珍有什么事情,我就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不放过你们谢家!”
谢京福瞬间清醒了,他看到父亲依旧站在里边,颤巍巍地跺着拐杖,说:“打,使劲打,他兰姨,你放心,就是你打死了他,我谢慎也决不会说一个‘不’字,他是罪有应得,他活该!”
谢京福被这情景惊得魂飞魄散,他知道定然是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于是,他抓住兰姨的手说:“兰姨,发生什么了?请告诉我,该我负责的我一定负责。”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