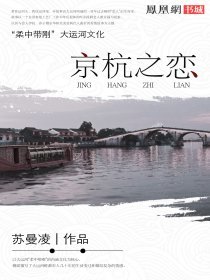第九章 生离死别1
兰姨一听,捂着嘴,仰天哭泣起来:“你怎么负责?人都快断气了,你怎么负责呀?万一慧珍出了什么意外,让我怎么和她父母交代呀!”
“兰姨,慧珍她?”
“就是因为你拒绝了她,她一伤心,就用刀子割了自己的手腕,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我苦命的外甥女呀,真是傻透了,为什么非要看上这样一个愣头男人,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值不值得呀?”
兰姨的泪水飞溅到谢京福的衣服上,他就这样任凭兰姨打骂着,动也不动。
“混账小子,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医院看看!”
谢京福被父亲这一声惊雷似的呼喊给惊醒了,他点了点头,转身就飞奔了出去。他没有想到,曹慧珍是这样一个烈性女子,她以这样决绝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问过了护士,才终于找到了曹慧珍所住的病房,也看到曹慧珍的家人都已经从天津赶来。听说经过大半天折腾,已经过了危险期,等着醒来就可以了,谢京福听着方才松了一口气。
他刚刚转身,就看到一个身穿中山服、带着黑框眼镜,肃穆而立的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冷冷地说:“我是曹慧珍的父亲,你就是做珐琅的那个谢京福?”
谢京福不安地点头:“是,是我,对不起慧珍。”
曹慧珍的父亲鼓起脸,似乎强行按捺住自己胸中的怒气,说道:“我们的家慧珍是个至情至性的女子,你对她好一分,她就会还你十分。她的心也大,从来不抱怨,也知道替人着想。没想到,你看着貌不惊人,还真是挺有本事的,还真把我们的慧珍逼到绝路上来了。”
谢京福的喉咙开始热了,他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只知道自己此刻说什么都是无用的,所有的辩白在一次几乎毁灭生命的历程中都显得微不足道。他只有说一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他听到曹慧珍家人有人说:“对这样的人渣,还和他客气什么?”
面对群情汹涌、几乎要裂炸的场面,谢京福闭上眼睛,知道这一场劫,是自己生命中避不开的,不如就迎上前去,接受惩罚。也许,肉体的痛疼可以抵挡那失去挚爱的绝望。
但是,他听到有人说:“曹慧珍醒了,家属可以进去了。”
他听了精神一震,随后又听到曹慧珍的父亲进去又出来,对自己说:“慧珍让你进去。”
他愣了愣,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于是点了点头,径直朝病房里走去。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上,曹慧珍的发丝凌乱,没有血色的脸被一束暖暖的阳光照着,似乎多了几分生机。吊瓶高高悬挂着,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正缓缓流入血管里,安静下来的曹慧珍,有着小家碧玉的温婉,也有着大家闺秀的矜持。她忽然朝谢京福一笑,嘶哑的声音重重敲击到谢京福的心里。
“谢大哥,我不怪你,都是我自己想不开,我没有替你着想,现在我的家人为难你了吧?”
“不,不要说了!”谢京福的泪水顿时倾泄而出,他忍不住了,这姑娘再多的付出,自己也还不起,正如自己说的那句话,他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再也装不下别人了。
“谢大哥,你放心,这次我是一时冲动,人常说冲动是魔鬼,这次我可能真的中了邪魔了,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其实也很明白,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本来就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怪不得你的,你并没有承诺过我什么。这次我重新活了一次,自然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爱是成全与付出,不是强取豪夺的自私,所以我愿意退出,谢大哥,你去找你爱的姑娘吧!我以后不会再扰你了。”
谢京福听得连连点头,哽咽起来。他看到曹慧珍的笑容是真实的,和她的本性一样,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矫揉造作,他无法说出什么,只好站立起来,朝曹慧珍深深鞠了一个躬,然后便缓缓地走出病房。打开门,门口都是对自己怒目而视的曹家人,他只好低头向每个人一一鞠躬。
曹慧珍的苏醒和剖白让其父情绪平静了很多,他摆了摆手说:“生气归生气,但是我们也是有眼睛看的。在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将你撕成碎片,但是看到你以后,我就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匠人的眼神,你的眼神里是干净的,我也知道你不会欺骗慧珍,想来都是她的心结,现在她已经无碍,你可以走了。”
谢京福听了,又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他面对着深受感情折磨的曹慧珍,纵然有千般万般的不忍,但最终还是拗不过自己的心。他明明知道,只要自己说一声,愿意和她结婚,她也许会活蹦乱跳。他明明知道,自己再也追不回心爱的姑娘了,也不愿意接受一个走不进自己心里的女人。
夜晚的风很凉,路边的落叶飞旋着,飘荡在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大地。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看到家里一只破旧的木钟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一点,父亲依然没有睡,只是依旧抽着烟,默默地盯着自己。
谢慎叹了口气,说:“洗洗睡吧!我也不想说你,我们谢家男儿都是这种脾气,我自己也是苦了一辈子,焉能不知道你的心思,只是这样,到头来,我们谢家还有传承人吗?”
谢京福想了想,答道:“爹,我知道,你从来没和我说实话,我娘她并没有死,是吗?那时候,我虽然才两岁,可是并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谢慎震惊了一下,眼神浑浊起来:“不提她了。对你来说,她就是一场梦,醒了,梦就没了,当她不存在就好。”
“是的,我是可以当她不存在,可是您呢?这些年您一直没有续娶,难道是只是因为我吗?还是因为做珐琅没工夫想自己的事?”
谢慎的心事被儿子击中,顿时恼火:“我说你一句,你就还一片!我是你的老子,你还编排我的不是。我奉劝你一句,你不喜欢的可以不要,但是你喜欢的又得不来,想也没有用,不如趁早收了心,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是编排您,只是替您痛。为什么您可以放不下一个人,我却不可以?”
“混账!”谢慎骂了一句,恍然觉得自己的心脏有些不舒服,就缓缓地坐下来,颓靡地说,“你既然知道我是你老子,你老子是过来人,知道这苦,所以不希望你再和我一样……去吧,不要说了,那屋里还有我给你留的作业,睡不着就去干活!”
谢京福没有再顶撞父亲,只是用粗糙的大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走向自己熟悉的那件小工坊。自小到大,每当自己伤心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点上一根蜡烛,专注地做“点蓝”。
父亲留给他的是一只需要第二遍“点蓝”桃型天球瓶。工具和釉料已经备好,他又抹了一把泪,飞快地脱下那身已经到处都是褶皱的新衣服,换上了平常穿的工衣。夜色如水,烛光淡淡的,随着窗口吹入的清风飘忽着,蓝色的釉料散发着回归的意境,忽然,他觉得这才是自己的归宿。
这蓝色,折射出一种可以看到本真与初心的美,美得一尘不染,美得可以媲美明月星辰。
他顿时没有困意,蘸取了釉料,一点点灌注了下去。
许久以前,伊杭曾经也憧憬过自己的婚姻,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应该就是嫁一个志同道合的男子,花前月下,被宠溺着,相夫教子之闲,悬腕挥毫,画上几幅画,那日子虽然是普通人家最日常的闲淡,却是最幸福的。但她看到那个日益残败的家,那份梦幻逐渐还原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她就好比折翼的鸟,不过是凭着几分残留的气力在地面上扑腾几下,最后还是要雌伏于生活的无奈与艰辛,她最终还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命运。
伊杭的新婚之夜,不但没有普通人的柔情蜜意,而且着实是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高俊山有三个儿子,长子高学胜、次子高学勇都已经结婚,听说年幼时就是这城里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任谁都不敢得罪。而第三个儿子高学辉则自三岁时候,就是一只桀骜不驯的小马驹子,高俊山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去抚养,听说他不到十二岁就早早辍学,任何人都拿捏不了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为此,高俊山也很是头疼,却毫无办法,只能听任他去。
此刻,高学辉在外边游荡未归,家里只是这两个儿子便让高俊山和伊杭颇为苦恼。他们并不喜欢伊杭,对于父亲的这场婚事丝毫不在意,只是碍于父亲的面子不得不忍了下来。
伊杭与高俊山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才累得精疲力竭地回到婚房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高学胜和高学勇不仅把亲生母亲的遗像放到了伊杭与高俊山的婚房里,还带着几个不知道哪里找来的小混混,在婚房里摆了一桌子麻将,几个人喝得东倒西歪,骂声不断。
高俊山被激怒了,借着酒劲朝几个人重重踢了过去,几个人看了看,形势不好,便纷纷借故走了
“他娘的,你们把老子的婚事搞得乌烟瘴气,是什么居心?”
高学胜冷冷笑了一声:“我们的妈刚刚过世不到半年,您老就老牛吃嫩草,给我们找了个小妈来,您说说,我们在北京城里可怎么混?”
“我的事是我的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就没关系了?这个小妈听说还是什么贵族之后,我们看她那眼睛,满眼都是铜臭,活脱脱一个居心叵测的美女蛇!您看人家就不想想,人家不看中我家的钱,谁会嫁给您这个快入土的老头子?”
“屁话!咒你们的爸死?今儿是我的大喜日子,哪个再敢胡说八道,这家的财产谁就别想得到!”
听到这里,二儿子高学勇一把将麻将推到到一边,对躲在高俊山身后的伊杭说:“我说小妈,您可真有一套,刚刚进门,就用离间计,教唆老爷子疏远自己的亲生儿子,您可真有本事,真让我们看走了眼。”
伊杭这才发现,无论自己原来做好了多少准备,当面临这几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继子的舌枪唇剑之时,还是有些难以承受。
她将眼泪憋了回去,说道:“都说是先入为主,我虽然比不了你们母亲和你们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但是我也是你父亲明媒正娶回来的妻室,所以无论你们都多少不满,但我还是你们的长辈。在你们说话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是否站住了脚,是否配的上你们的身份?”
高学胜惊讶地说了一句:“怪不得我家老爷子被你迷得五迷三道的,原来你还真是不简单呢!什么身份,是你那所谓的什么满族格格身份?哈哈哈……可笑,告诉你,我们很清楚自己是这个家的人,倒是你,满脑子龌龊思想的女人,别想挡着我们兄弟的路,小心我们给颜色看!”
一直在旁边吸着烟不语的高学勇终于将嘴里的烟头一口吐了出去,指着伊杭的鼻子说:“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就算老爷子再疼你,但是难道他真的能保你一辈子?笑话,你这真是自不量力,还想着我高家的财产,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想都别想。”
伊杭嗫嚅着,想辩白自己:“我没有你们想的那样龌龊,我是遇到一些难处,但是我也会付出代价,尽力对这个家好,所以,你们暂且不要再说什么,还是看看我到底做了什么?”
高俊山早已经按捺不去,走过去,朝着两个人儿子一人一掌,骂了起来:“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出去,今天是老子的好日子,都被你们搅了!现在老子还活着,由不得你们猖狂,既然是老子说了算,你们都给我闭嘴,老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高学胜捂着脸,恨恨地朝外走:“老三还不知道这个事,我看到时候他回来了,你们怎么收场?老二,我们走!这里呆不得了,满屋子都是骚狐狸味儿,受不了!”
高学勇冷笑了一声,也跟着出了门。
看着满屋子狼藉,到处散发着浑浊的酒气与臭气,伊杭意识到,树欲静而风不止,自己从来没有就没有安然享受生活的命运,这一生,怕是要卷入另外一场看不到底的漩涡里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无奈?高俊山并没有对自己不好,只是他改变不了商人的本性,即便是帮自己偿还了所有的债务,也是要自己这个人来换取这种恩赐,对于高俊山来说,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利大于本,并不算很亏。
他正想着,只听高俊山说:“还好,幸亏我有所准备,这屋子里值钱的东西我早给藏了,就是怕这两个忤逆不孝的家伙打这些东西的主意,看来,我这心还真没有白费。”
伊杭听着高俊山这些话,心早已经凉了,她默默地收拾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忽然感觉到腰被紧紧抱住了,只听身后高俊山借着酒意大声喘息着:“别忙了,我的宝贝!以前是想都不敢想,你能成了我的媳妇儿!这也算是老天可怜我一生不易,你放心,我会疼人的,也会照顾好你的家人。来,别看我年级大了,但是身子骨好着呢!咱们再生一个儿子给他们看看……”
伊杭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瑟缩起来,窗外清风袭来,花香醉人,她的眼泪却潸潸而下……酒气与肉体的侵入越来越近,她索性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在黑暗中接受这一切。
“兰姨,慧珍她?”
“就是因为你拒绝了她,她一伤心,就用刀子割了自己的手腕,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我苦命的外甥女呀,真是傻透了,为什么非要看上这样一个愣头男人,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值不值得呀?”
兰姨的泪水飞溅到谢京福的衣服上,他就这样任凭兰姨打骂着,动也不动。
“混账小子,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医院看看!”
谢京福被父亲这一声惊雷似的呼喊给惊醒了,他点了点头,转身就飞奔了出去。他没有想到,曹慧珍是这样一个烈性女子,她以这样决绝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问过了护士,才终于找到了曹慧珍所住的病房,也看到曹慧珍的家人都已经从天津赶来。听说经过大半天折腾,已经过了危险期,等着醒来就可以了,谢京福听着方才松了一口气。
他刚刚转身,就看到一个身穿中山服、带着黑框眼镜,肃穆而立的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冷冷地说:“我是曹慧珍的父亲,你就是做珐琅的那个谢京福?”
谢京福不安地点头:“是,是我,对不起慧珍。”
曹慧珍的父亲鼓起脸,似乎强行按捺住自己胸中的怒气,说道:“我们的家慧珍是个至情至性的女子,你对她好一分,她就会还你十分。她的心也大,从来不抱怨,也知道替人着想。没想到,你看着貌不惊人,还真是挺有本事的,还真把我们的慧珍逼到绝路上来了。”
谢京福的喉咙开始热了,他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只知道自己此刻说什么都是无用的,所有的辩白在一次几乎毁灭生命的历程中都显得微不足道。他只有说一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他听到曹慧珍家人有人说:“对这样的人渣,还和他客气什么?”
面对群情汹涌、几乎要裂炸的场面,谢京福闭上眼睛,知道这一场劫,是自己生命中避不开的,不如就迎上前去,接受惩罚。也许,肉体的痛疼可以抵挡那失去挚爱的绝望。
但是,他听到有人说:“曹慧珍醒了,家属可以进去了。”
他听了精神一震,随后又听到曹慧珍的父亲进去又出来,对自己说:“慧珍让你进去。”
他愣了愣,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于是点了点头,径直朝病房里走去。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上,曹慧珍的发丝凌乱,没有血色的脸被一束暖暖的阳光照着,似乎多了几分生机。吊瓶高高悬挂着,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正缓缓流入血管里,安静下来的曹慧珍,有着小家碧玉的温婉,也有着大家闺秀的矜持。她忽然朝谢京福一笑,嘶哑的声音重重敲击到谢京福的心里。
“谢大哥,我不怪你,都是我自己想不开,我没有替你着想,现在我的家人为难你了吧?”
“不,不要说了!”谢京福的泪水顿时倾泄而出,他忍不住了,这姑娘再多的付出,自己也还不起,正如自己说的那句话,他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再也装不下别人了。
“谢大哥,你放心,这次我是一时冲动,人常说冲动是魔鬼,这次我可能真的中了邪魔了,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其实也很明白,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本来就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怪不得你的,你并没有承诺过我什么。这次我重新活了一次,自然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爱是成全与付出,不是强取豪夺的自私,所以我愿意退出,谢大哥,你去找你爱的姑娘吧!我以后不会再扰你了。”
谢京福听得连连点头,哽咽起来。他看到曹慧珍的笑容是真实的,和她的本性一样,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矫揉造作,他无法说出什么,只好站立起来,朝曹慧珍深深鞠了一个躬,然后便缓缓地走出病房。打开门,门口都是对自己怒目而视的曹家人,他只好低头向每个人一一鞠躬。
曹慧珍的苏醒和剖白让其父情绪平静了很多,他摆了摆手说:“生气归生气,但是我们也是有眼睛看的。在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将你撕成碎片,但是看到你以后,我就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匠人的眼神,你的眼神里是干净的,我也知道你不会欺骗慧珍,想来都是她的心结,现在她已经无碍,你可以走了。”
谢京福听了,又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他面对着深受感情折磨的曹慧珍,纵然有千般万般的不忍,但最终还是拗不过自己的心。他明明知道,只要自己说一声,愿意和她结婚,她也许会活蹦乱跳。他明明知道,自己再也追不回心爱的姑娘了,也不愿意接受一个走不进自己心里的女人。
夜晚的风很凉,路边的落叶飞旋着,飘荡在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大地。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看到家里一只破旧的木钟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一点,父亲依然没有睡,只是依旧抽着烟,默默地盯着自己。
谢慎叹了口气,说:“洗洗睡吧!我也不想说你,我们谢家男儿都是这种脾气,我自己也是苦了一辈子,焉能不知道你的心思,只是这样,到头来,我们谢家还有传承人吗?”
谢京福想了想,答道:“爹,我知道,你从来没和我说实话,我娘她并没有死,是吗?那时候,我虽然才两岁,可是并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谢慎震惊了一下,眼神浑浊起来:“不提她了。对你来说,她就是一场梦,醒了,梦就没了,当她不存在就好。”
“是的,我是可以当她不存在,可是您呢?这些年您一直没有续娶,难道是只是因为我吗?还是因为做珐琅没工夫想自己的事?”
谢慎的心事被儿子击中,顿时恼火:“我说你一句,你就还一片!我是你的老子,你还编排我的不是。我奉劝你一句,你不喜欢的可以不要,但是你喜欢的又得不来,想也没有用,不如趁早收了心,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是编排您,只是替您痛。为什么您可以放不下一个人,我却不可以?”
“混账!”谢慎骂了一句,恍然觉得自己的心脏有些不舒服,就缓缓地坐下来,颓靡地说,“你既然知道我是你老子,你老子是过来人,知道这苦,所以不希望你再和我一样……去吧,不要说了,那屋里还有我给你留的作业,睡不着就去干活!”
谢京福没有再顶撞父亲,只是用粗糙的大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走向自己熟悉的那件小工坊。自小到大,每当自己伤心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点上一根蜡烛,专注地做“点蓝”。
父亲留给他的是一只需要第二遍“点蓝”桃型天球瓶。工具和釉料已经备好,他又抹了一把泪,飞快地脱下那身已经到处都是褶皱的新衣服,换上了平常穿的工衣。夜色如水,烛光淡淡的,随着窗口吹入的清风飘忽着,蓝色的釉料散发着回归的意境,忽然,他觉得这才是自己的归宿。
这蓝色,折射出一种可以看到本真与初心的美,美得一尘不染,美得可以媲美明月星辰。
他顿时没有困意,蘸取了釉料,一点点灌注了下去。
许久以前,伊杭曾经也憧憬过自己的婚姻,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应该就是嫁一个志同道合的男子,花前月下,被宠溺着,相夫教子之闲,悬腕挥毫,画上几幅画,那日子虽然是普通人家最日常的闲淡,却是最幸福的。但她看到那个日益残败的家,那份梦幻逐渐还原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她就好比折翼的鸟,不过是凭着几分残留的气力在地面上扑腾几下,最后还是要雌伏于生活的无奈与艰辛,她最终还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命运。
伊杭的新婚之夜,不但没有普通人的柔情蜜意,而且着实是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高俊山有三个儿子,长子高学胜、次子高学勇都已经结婚,听说年幼时就是这城里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任谁都不敢得罪。而第三个儿子高学辉则自三岁时候,就是一只桀骜不驯的小马驹子,高俊山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去抚养,听说他不到十二岁就早早辍学,任何人都拿捏不了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为此,高俊山也很是头疼,却毫无办法,只能听任他去。
此刻,高学辉在外边游荡未归,家里只是这两个儿子便让高俊山和伊杭颇为苦恼。他们并不喜欢伊杭,对于父亲的这场婚事丝毫不在意,只是碍于父亲的面子不得不忍了下来。
伊杭与高俊山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才累得精疲力竭地回到婚房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高学胜和高学勇不仅把亲生母亲的遗像放到了伊杭与高俊山的婚房里,还带着几个不知道哪里找来的小混混,在婚房里摆了一桌子麻将,几个人喝得东倒西歪,骂声不断。
高俊山被激怒了,借着酒劲朝几个人重重踢了过去,几个人看了看,形势不好,便纷纷借故走了
“他娘的,你们把老子的婚事搞得乌烟瘴气,是什么居心?”
高学胜冷冷笑了一声:“我们的妈刚刚过世不到半年,您老就老牛吃嫩草,给我们找了个小妈来,您说说,我们在北京城里可怎么混?”
“我的事是我的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就没关系了?这个小妈听说还是什么贵族之后,我们看她那眼睛,满眼都是铜臭,活脱脱一个居心叵测的美女蛇!您看人家就不想想,人家不看中我家的钱,谁会嫁给您这个快入土的老头子?”
“屁话!咒你们的爸死?今儿是我的大喜日子,哪个再敢胡说八道,这家的财产谁就别想得到!”
听到这里,二儿子高学勇一把将麻将推到到一边,对躲在高俊山身后的伊杭说:“我说小妈,您可真有一套,刚刚进门,就用离间计,教唆老爷子疏远自己的亲生儿子,您可真有本事,真让我们看走了眼。”
伊杭这才发现,无论自己原来做好了多少准备,当面临这几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继子的舌枪唇剑之时,还是有些难以承受。
她将眼泪憋了回去,说道:“都说是先入为主,我虽然比不了你们母亲和你们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但是我也是你父亲明媒正娶回来的妻室,所以无论你们都多少不满,但我还是你们的长辈。在你们说话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是否站住了脚,是否配的上你们的身份?”
高学胜惊讶地说了一句:“怪不得我家老爷子被你迷得五迷三道的,原来你还真是不简单呢!什么身份,是你那所谓的什么满族格格身份?哈哈哈……可笑,告诉你,我们很清楚自己是这个家的人,倒是你,满脑子龌龊思想的女人,别想挡着我们兄弟的路,小心我们给颜色看!”
一直在旁边吸着烟不语的高学勇终于将嘴里的烟头一口吐了出去,指着伊杭的鼻子说:“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就算老爷子再疼你,但是难道他真的能保你一辈子?笑话,你这真是自不量力,还想着我高家的财产,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想都别想。”
伊杭嗫嚅着,想辩白自己:“我没有你们想的那样龌龊,我是遇到一些难处,但是我也会付出代价,尽力对这个家好,所以,你们暂且不要再说什么,还是看看我到底做了什么?”
高俊山早已经按捺不去,走过去,朝着两个人儿子一人一掌,骂了起来:“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出去,今天是老子的好日子,都被你们搅了!现在老子还活着,由不得你们猖狂,既然是老子说了算,你们都给我闭嘴,老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高学胜捂着脸,恨恨地朝外走:“老三还不知道这个事,我看到时候他回来了,你们怎么收场?老二,我们走!这里呆不得了,满屋子都是骚狐狸味儿,受不了!”
高学勇冷笑了一声,也跟着出了门。
看着满屋子狼藉,到处散发着浑浊的酒气与臭气,伊杭意识到,树欲静而风不止,自己从来没有就没有安然享受生活的命运,这一生,怕是要卷入另外一场看不到底的漩涡里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无奈?高俊山并没有对自己不好,只是他改变不了商人的本性,即便是帮自己偿还了所有的债务,也是要自己这个人来换取这种恩赐,对于高俊山来说,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利大于本,并不算很亏。
他正想着,只听高俊山说:“还好,幸亏我有所准备,这屋子里值钱的东西我早给藏了,就是怕这两个忤逆不孝的家伙打这些东西的主意,看来,我这心还真没有白费。”
伊杭听着高俊山这些话,心早已经凉了,她默默地收拾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忽然感觉到腰被紧紧抱住了,只听身后高俊山借着酒意大声喘息着:“别忙了,我的宝贝!以前是想都不敢想,你能成了我的媳妇儿!这也算是老天可怜我一生不易,你放心,我会疼人的,也会照顾好你的家人。来,别看我年级大了,但是身子骨好着呢!咱们再生一个儿子给他们看看……”
伊杭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瑟缩起来,窗外清风袭来,花香醉人,她的眼泪却潸潸而下……酒气与肉体的侵入越来越近,她索性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在黑暗中接受这一切。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