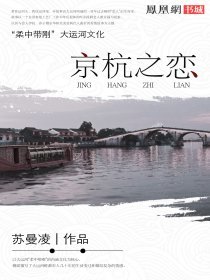第九章 生离死别2
谢京福没有想到,这一次不仅仅是伤害了曹慧珍,也彻底终结了与兰姨多年的邻居情分。曹慧珍痊愈后,关了裁缝店,跟随家里回了天津。而兰姨并不原谅谢家父子,一怒之下,将房子卖给了一家外地人,搬离了这里,也彻底和谢家断绝了缘分。
父亲只是叹气说:“好,好,断了好,不该结的缘就随他去吧!”
谢京福照例每天都拉着人力车和黄玉斌到什刹海去跑。一次,他拉着一位客人路过东安市场,依稀看到伊杭跟着高俊山走进了一家画廊,他看到伊杭的脸上是带着笑容的,他知道自己的担心多余了,于是便狠了狠心,扭转过头,不再看他们。
那盒花青依旧还在自己手里,也许,随着自己对过去的淡忘,会成为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放下与成全,才是匠师的境界。在这烟火人生里,也是考验一个珐琅匠师的心智与德行。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当香山的红叶刚刚开始泛红的时候,他拉了一对海外归国华侨,畅游什刹海。那是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妻子喜欢中国的手工艺术品,一时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她不知道从哪里淘到一只紫红双色兰花珐琅胸针,便对自己的丈夫说:“你不是说,要给买生日礼物吗?我喜欢景泰蓝那样的艺术瓶子,但是这次看了几个地方,都没有买到喜欢的,我们的签证就快到期了,难道真的就这样遗憾着回去吗?”
丈夫只好劝说:“我们中国的器皿肯定是带着中国元素,什么天圆地方,什么天地人和,什么福禄寿禧你都看了,还是不满意,不然就是质量差些,掂在手里轻飘飘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能买,不是吗?”
妻子说:“你也知道,我买这瓶子是为了给母亲大人过八十大寿用的,母亲离开中国多年了,只想要这样一件中国自己做的东西,我还不能满足她老人家吗?”
谢京福听了,心中一动,忍不住问那老妇人:“夫人,您想要什么样的景泰蓝瓶?也许,我可以给您些参考建议。”
那老夫人拍着手高兴极了:“差点忘记了,师傅们成天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知道哪里有好货,给我们说说也好。”
谢京福抬头看到天色已晚,说:“我先把您二位送到酒店,如果您放心,相信我,明天一早我自会带着珐琅瓶给您们送过去。”
“真的?说的也对,中国的民间都是高手、大师,我们相信您,那好,师傅,明天您来就到酒店找我们。”
谢京福将两位老夫妇送到酒店后,回到家找了两套珐琅艺术瓶精品,装好了,第二天打算亲自送到酒店,没想到刚刚出门,就看到黄玉斌大呼小叫地冲过来,拉着谢京福的手喊着:“你这是要做什么?”
“去送珐琅瓶。”
“发生了大事啦!赶紧和我走,还送什么珐琅瓶呀!”
谢京福一头雾水被黄玉斌拉扯着往前走了几步,终于甩开了他,恼怒道:“你小子又发什么疯?”
黄玉斌“哈哈”大笑,说:“这回我们的春天可真是来了,国家要成立公私合营珐琅厂,现在正招工呢!说是只要有一定珐琅技术的人都可以去报名,尤其是以前在民间私人作坊有过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这次我们要是被招工了,可就是国家正式职工了,可就是铁饭碗了。”
谢京福听到愣住了:“真的?”
“千真万确!”黄玉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儿,他朝谢京福喊着,“以后我们可就有出路了!还不赶紧走!”
“好,你等我放下东西换件干净衣服就去。”谢京福说话的时候都带了颤音,他并不知觉,只是愧疚要对老夫妇食言了,怕是要到晚一点才能送去了。他挑的是一副卧冰求鲤的六棱瓶和一个芦花顺母的广口瓶,这是他和自己父亲共同完成了,也是最用心的两个精品。
谢京福和父亲说了一声,就和黄玉斌到了珐琅厂的招工地址,他没有想到,这里集聚了很多以前就熟悉的老朋友,看到有一位主管人事的李副厂长正笑着说:“我们这里最欢迎珐琅世家的子弟,这种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的,我们更需要有创作力的工匠,经过我们的培养,以后还会成为一流的国际大师,大家要加油呀!”
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谢京福与大家一样,心中这股不甘沉沦的心已经憋了很久,此刻终于得到了释放。这也是自从伊杭出嫁以后,谢京福最快乐的一天。他们报名回来,一路拍着手,笑得让路人纷纷侧目。
街道上的黄菊花开得灿烂,密密麻麻的花瓣舒卷着,含苞欲放,朝行人盛放自己淡泊的情怀。谢京福看到这色彩,心中已经笃定,要调出一款比孔雀绿色的釉料来。浓黄色与蓝色经过配比,就是最好看的绿色。景泰蓝可以是蓝色,也可以有更色彩斑斓的前景与未来。接下来就是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了。
谢京福回到家,重新取了两只珐琅瓶,匆匆赶到老夫妇下塌的酒店。没想到前台告诉谢京福说,老夫妇刚刚离开。谢京福只好失望地往外走,这时,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说让你再检查一遍,你就不听。”
“我就是最喜欢那个蓝花珐琅胸针,就是要找回来,还有遗憾的就是那个拉人力车的师傅没来,看来这一次我们真要失望了。”
谢京福嘴角一咧,笑了。他迅速转身,朝着那老夫妇走去:“先生,夫人,实在对不起,由于我忽然遇到一件紧急的事情,所以才耽误了过来的时间,实在是对不起了。”
谢京福的从天而降显然也让老夫妇惊呆了,他们转而兴奋地说:“亏得我的胸花丢了,不然还真是错过了。”
老夫妇从服务台找到了自己丢的东西,然后打开谢京福送来的两只瓶子,顿时惊喜交加:“天哪,没想到我们临走前还会看到这样的景泰蓝精品,太喜欢了,这两只都要了。请问这瓶子是哪位大师的作品,我们想留个联系方式,我先生是在外贸生意的,也许以后我们还可以有往来。”
谢京福低着头说:“这是我和家父共同完成的作品,不是什么大师?”
“什么?您和您的父亲?”妻子惊得目瞪口呆,“我也是学艺术的,知道这种工艺可不是一朝一夕才能练就的,这个可是几十年的功力呢!请问您是?”
谢京福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谢家从清朝乾隆年间,就给满清皇家做珐琅器,后来专门为富察氏贝子府做家匠,从民国到现在,一直在民间经营作坊。不过,现在好了,国家以后有了景泰蓝厂,我们珐琅匠人就有依托了。”
“天哪!”老妇人听着这话,惊讶地捂着嘴说,“原来得来不白费功夫,真正的高手果然隐藏在民间,真是对不住了,大师。”
谢京福被这声“大师”叫得面红耳赤,连忙说:“不,不,还差得远,我家世代就是手艺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谈大师可有些远了。”
男子听到这些,连忙说:“请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以后我们可以再联系。”
谢京福说:“以后我成了珐琅厂的职工,您到珐琅厂来找我就是了,我叫谢京福。”
“好。”老夫妇连连点头。
谢京福回来的时候,生平有了人家所说的价值感,这种感觉是饱满而带有生机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将自己心头那固执的疼痛暂时遏制,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存在。
深秋是寒凉的,四周行人和谢京福一样匆忙迈着归家的脚步,似乎已经将这些寒冷忽略。远远望去,万家灯火,就这般不经意地将迎接美好未来的激情渐渐点燃。古老的红色建筑在这种感性的映照下,也呈现着最令人感动的画面。
果然和谢京福心中所料一样,没过多久,谢京福与黄玉斌就接到了珐琅厂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上写着,第一天入场要进行一场考试,考的就是掐丝工艺。掐丝是最考验耐性的工作,这是别具一格的艺术与经年累月的细作相融合的过程。谢京福淡笑,这是自己最擅长的,这份技艺在自己熟悉的珐琅工群体中,自己也是最快的,他笃定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认可。
这次考试用的铜胎是已经打制好的,谢京福的是一只乾隆时期风格的碗,而黄玉斌的是一只小扁瓶子,其他人则是笔洗、首饰盒等小件器皿。谢京福知道这次为了节约成本,他看到自己的纹饰是自己最擅长的菊花,而黄玉斌的恰恰是他很少掐过的牡丹花。这两种花卉花瓣都是重叠纵深,要求非常精细。
果然,他看到黄玉斌蹙起了眉头,悄悄地对谢京福说:“福哥,你知道我,我们换换吧?”
谢京福摇头说:“这是考试的规定,我们不能弄虚作假。”
黄玉斌有些不满小声嘀咕着:“见死不救,不够意思。”
谢京福瞥了他一眼,说:“沉住气,手不要抖,先大后小,由上至下,你想想以前给洋人做大瓶时候,你师傅说的什么。我信你。”他看到黄玉斌唉声叹气地拿着镊子发呆,原来那牡丹的花瓣折角比菊花更加复杂,除了要掐出完整的花瓣,还有很多半弧形要掐出来,他看到黄玉斌掐出来的不是大就是小,还有的形状与设计图差的太远了,不由摇头。
黄玉斌的性子急躁豪气,善于山水画和鸡鸟虫鱼的写生与铜丝制作,最欠缺的就是这花卉的基本功。于是他故意咳嗽了一声,拿起一个圆柱形的模具,将铜丝一圈圈裹了上去,然后再小心拆取下来,用剪子顺着一圈圈的铜丝一下子就剪了下去,那些铜丝瞬间见变成了半圈了。再用镊子轻轻一捏,一个角就出来了,再一捏,又一个角就出来了。
黄玉斌似乎懂得了谢京福的一片苦心,原来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这样简单借助外力来完成。他脑海中如醍醐灌顶“轰”地响了一下,他忽然想到该怎样制作那些小而精美的花丝了。于是,他拿起自己手里的铅笔,将铜丝绕了几圈,然后给剪断,再用小镊子一点点塑形,很快,那些铜丝就变得温驯了,变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父亲只是叹气说:“好,好,断了好,不该结的缘就随他去吧!”
谢京福照例每天都拉着人力车和黄玉斌到什刹海去跑。一次,他拉着一位客人路过东安市场,依稀看到伊杭跟着高俊山走进了一家画廊,他看到伊杭的脸上是带着笑容的,他知道自己的担心多余了,于是便狠了狠心,扭转过头,不再看他们。
那盒花青依旧还在自己手里,也许,随着自己对过去的淡忘,会成为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放下与成全,才是匠师的境界。在这烟火人生里,也是考验一个珐琅匠师的心智与德行。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当香山的红叶刚刚开始泛红的时候,他拉了一对海外归国华侨,畅游什刹海。那是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妻子喜欢中国的手工艺术品,一时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她不知道从哪里淘到一只紫红双色兰花珐琅胸针,便对自己的丈夫说:“你不是说,要给买生日礼物吗?我喜欢景泰蓝那样的艺术瓶子,但是这次看了几个地方,都没有买到喜欢的,我们的签证就快到期了,难道真的就这样遗憾着回去吗?”
丈夫只好劝说:“我们中国的器皿肯定是带着中国元素,什么天圆地方,什么天地人和,什么福禄寿禧你都看了,还是不满意,不然就是质量差些,掂在手里轻飘飘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能买,不是吗?”
妻子说:“你也知道,我买这瓶子是为了给母亲大人过八十大寿用的,母亲离开中国多年了,只想要这样一件中国自己做的东西,我还不能满足她老人家吗?”
谢京福听了,心中一动,忍不住问那老妇人:“夫人,您想要什么样的景泰蓝瓶?也许,我可以给您些参考建议。”
那老夫人拍着手高兴极了:“差点忘记了,师傅们成天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知道哪里有好货,给我们说说也好。”
谢京福抬头看到天色已晚,说:“我先把您二位送到酒店,如果您放心,相信我,明天一早我自会带着珐琅瓶给您们送过去。”
“真的?说的也对,中国的民间都是高手、大师,我们相信您,那好,师傅,明天您来就到酒店找我们。”
谢京福将两位老夫妇送到酒店后,回到家找了两套珐琅艺术瓶精品,装好了,第二天打算亲自送到酒店,没想到刚刚出门,就看到黄玉斌大呼小叫地冲过来,拉着谢京福的手喊着:“你这是要做什么?”
“去送珐琅瓶。”
“发生了大事啦!赶紧和我走,还送什么珐琅瓶呀!”
谢京福一头雾水被黄玉斌拉扯着往前走了几步,终于甩开了他,恼怒道:“你小子又发什么疯?”
黄玉斌“哈哈”大笑,说:“这回我们的春天可真是来了,国家要成立公私合营珐琅厂,现在正招工呢!说是只要有一定珐琅技术的人都可以去报名,尤其是以前在民间私人作坊有过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这次我们要是被招工了,可就是国家正式职工了,可就是铁饭碗了。”
谢京福听到愣住了:“真的?”
“千真万确!”黄玉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儿,他朝谢京福喊着,“以后我们可就有出路了!还不赶紧走!”
“好,你等我放下东西换件干净衣服就去。”谢京福说话的时候都带了颤音,他并不知觉,只是愧疚要对老夫妇食言了,怕是要到晚一点才能送去了。他挑的是一副卧冰求鲤的六棱瓶和一个芦花顺母的广口瓶,这是他和自己父亲共同完成了,也是最用心的两个精品。
谢京福和父亲说了一声,就和黄玉斌到了珐琅厂的招工地址,他没有想到,这里集聚了很多以前就熟悉的老朋友,看到有一位主管人事的李副厂长正笑着说:“我们这里最欢迎珐琅世家的子弟,这种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的,我们更需要有创作力的工匠,经过我们的培养,以后还会成为一流的国际大师,大家要加油呀!”
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谢京福与大家一样,心中这股不甘沉沦的心已经憋了很久,此刻终于得到了释放。这也是自从伊杭出嫁以后,谢京福最快乐的一天。他们报名回来,一路拍着手,笑得让路人纷纷侧目。
街道上的黄菊花开得灿烂,密密麻麻的花瓣舒卷着,含苞欲放,朝行人盛放自己淡泊的情怀。谢京福看到这色彩,心中已经笃定,要调出一款比孔雀绿色的釉料来。浓黄色与蓝色经过配比,就是最好看的绿色。景泰蓝可以是蓝色,也可以有更色彩斑斓的前景与未来。接下来就是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了。
谢京福回到家,重新取了两只珐琅瓶,匆匆赶到老夫妇下塌的酒店。没想到前台告诉谢京福说,老夫妇刚刚离开。谢京福只好失望地往外走,这时,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说让你再检查一遍,你就不听。”
“我就是最喜欢那个蓝花珐琅胸针,就是要找回来,还有遗憾的就是那个拉人力车的师傅没来,看来这一次我们真要失望了。”
谢京福嘴角一咧,笑了。他迅速转身,朝着那老夫妇走去:“先生,夫人,实在对不起,由于我忽然遇到一件紧急的事情,所以才耽误了过来的时间,实在是对不起了。”
谢京福的从天而降显然也让老夫妇惊呆了,他们转而兴奋地说:“亏得我的胸花丢了,不然还真是错过了。”
老夫妇从服务台找到了自己丢的东西,然后打开谢京福送来的两只瓶子,顿时惊喜交加:“天哪,没想到我们临走前还会看到这样的景泰蓝精品,太喜欢了,这两只都要了。请问这瓶子是哪位大师的作品,我们想留个联系方式,我先生是在外贸生意的,也许以后我们还可以有往来。”
谢京福低着头说:“这是我和家父共同完成的作品,不是什么大师?”
“什么?您和您的父亲?”妻子惊得目瞪口呆,“我也是学艺术的,知道这种工艺可不是一朝一夕才能练就的,这个可是几十年的功力呢!请问您是?”
谢京福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谢家从清朝乾隆年间,就给满清皇家做珐琅器,后来专门为富察氏贝子府做家匠,从民国到现在,一直在民间经营作坊。不过,现在好了,国家以后有了景泰蓝厂,我们珐琅匠人就有依托了。”
“天哪!”老妇人听着这话,惊讶地捂着嘴说,“原来得来不白费功夫,真正的高手果然隐藏在民间,真是对不住了,大师。”
谢京福被这声“大师”叫得面红耳赤,连忙说:“不,不,还差得远,我家世代就是手艺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谈大师可有些远了。”
男子听到这些,连忙说:“请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以后我们可以再联系。”
谢京福说:“以后我成了珐琅厂的职工,您到珐琅厂来找我就是了,我叫谢京福。”
“好。”老夫妇连连点头。
谢京福回来的时候,生平有了人家所说的价值感,这种感觉是饱满而带有生机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将自己心头那固执的疼痛暂时遏制,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存在。
深秋是寒凉的,四周行人和谢京福一样匆忙迈着归家的脚步,似乎已经将这些寒冷忽略。远远望去,万家灯火,就这般不经意地将迎接美好未来的激情渐渐点燃。古老的红色建筑在这种感性的映照下,也呈现着最令人感动的画面。
果然和谢京福心中所料一样,没过多久,谢京福与黄玉斌就接到了珐琅厂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上写着,第一天入场要进行一场考试,考的就是掐丝工艺。掐丝是最考验耐性的工作,这是别具一格的艺术与经年累月的细作相融合的过程。谢京福淡笑,这是自己最擅长的,这份技艺在自己熟悉的珐琅工群体中,自己也是最快的,他笃定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认可。
这次考试用的铜胎是已经打制好的,谢京福的是一只乾隆时期风格的碗,而黄玉斌的是一只小扁瓶子,其他人则是笔洗、首饰盒等小件器皿。谢京福知道这次为了节约成本,他看到自己的纹饰是自己最擅长的菊花,而黄玉斌的恰恰是他很少掐过的牡丹花。这两种花卉花瓣都是重叠纵深,要求非常精细。
果然,他看到黄玉斌蹙起了眉头,悄悄地对谢京福说:“福哥,你知道我,我们换换吧?”
谢京福摇头说:“这是考试的规定,我们不能弄虚作假。”
黄玉斌有些不满小声嘀咕着:“见死不救,不够意思。”
谢京福瞥了他一眼,说:“沉住气,手不要抖,先大后小,由上至下,你想想以前给洋人做大瓶时候,你师傅说的什么。我信你。”他看到黄玉斌唉声叹气地拿着镊子发呆,原来那牡丹的花瓣折角比菊花更加复杂,除了要掐出完整的花瓣,还有很多半弧形要掐出来,他看到黄玉斌掐出来的不是大就是小,还有的形状与设计图差的太远了,不由摇头。
黄玉斌的性子急躁豪气,善于山水画和鸡鸟虫鱼的写生与铜丝制作,最欠缺的就是这花卉的基本功。于是他故意咳嗽了一声,拿起一个圆柱形的模具,将铜丝一圈圈裹了上去,然后再小心拆取下来,用剪子顺着一圈圈的铜丝一下子就剪了下去,那些铜丝瞬间见变成了半圈了。再用镊子轻轻一捏,一个角就出来了,再一捏,又一个角就出来了。
黄玉斌似乎懂得了谢京福的一片苦心,原来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这样简单借助外力来完成。他脑海中如醍醐灌顶“轰”地响了一下,他忽然想到该怎样制作那些小而精美的花丝了。于是,他拿起自己手里的铅笔,将铜丝绕了几圈,然后给剪断,再用小镊子一点点塑形,很快,那些铜丝就变得温驯了,变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