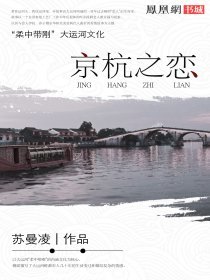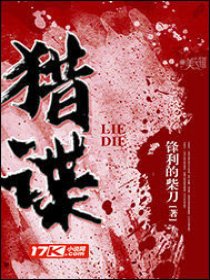第九章 生离死别3
不远处的谢京福看到黄玉斌喜笑颜开的样子,也淡淡笑了一下,继续做自己手里的工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谢京福越来越洞悉父亲的一片苦心,在父亲的教导下,他掌握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奇、巧、精与细的技巧,别人用三天才能做好的事情,他花了一天半就完成了,而且做工精细也是一流。这菊花是自小就跟着父亲学着掰出来的,那些菊花的图案早已经了然于心,即便是没有图纸,他只要看上一眼那图,随手就能掐出来。
谢京福看着自己已经做完的掐丝,还是觉得有一个小小的花瓣不够精致,看了看时间还早,于是屏住呼吸,轻轻按住那花瓣周围的铜丝,以防止它们连带掉落下来。把它轻轻拆了下来,又仔细一点点重新调整了几下,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当他把它完整地粘贴到铜胎上,他看到一个穿着中山服的人正微笑看着自己。他认识这个人,是入场时候就见过的,负责生产经营的李副厂长。
“你姓谢吧?是老北京城里鼎鼎大名的珐琅世家谢氏传人?”
谢京福站起身来,应了一声:“厂长您过誉了,不过就是家里传下来的是手艺活。做多了,自然就熟了。”
李副厂长握住了谢京福的手:“太好了,我看你这不用图纸就会掰花的技术,就知道你必定出身于老手艺人家,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样吧,你入场后直接跳过学徒工这个阶段,直接做带徒弟的匠师,工资也要比学徒工高一档。这样的人才,我们是大大欢迎呀!欢迎你们加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谢京福懵了,顿时觉的繁花满地,自己的心一点点暖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了一句:“为人民服务!”这句标语在街头小巷贴了很多,已经默默地记在自己心里,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句话居然和自己也扯上关系。
李副厂长又亲自拍着谢京福的肩膀说:“我们现在最需要你这样有经验的匠师带徒弟,你看看,还是年轻人多,他们还没能体会出这珐琅事业的艰辛,全靠师傅边教便带,当然还得教他们做人。我看到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就知道你的人品一定差不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四周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谢京福看着四周到处都是羡慕嫉妒的眼神,觉得胸腔里一股热流齐齐涌上,颤抖着说:“李厂长,我这水平恐怕还是欠缺。”
“安心做好你的传帮带师傅吧!厂里会支持你的。”
他郑重地看着李副厂长,还想推辞,却遭到了李厂长的决绝,无奈只好答应下来。
下班的时候,黄玉斌对谢京福说:“我说师兄,你走哪里都是星光灿烂呀!你一入场就当了师傅,工资还比别人高,我师傅可真是偏心,只把你教得这样出类拔萃,难道让我们这些师兄弟都去喝西北风?”
谢京福并不理睬他的胡搅蛮缠,只是狠狠朝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去你的!赶紧干正经事,你还不知道我家老爷子那人品?”
黄玉斌被打,不甘心地嚷着叫着,朝着前边奔跑谢京福追了过去。谢京福没有笑,想起父亲的话,做珐琅要心静,不要理睬别人的眼光,今后的生活更加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该何去何从。
谢京福也庆幸自己懂得父亲的一片苦心,珐琅厂卓越的资源也给了珐琅匠师们更多的滋养。谢京福以前与父亲是单打独斗,一番困难自是难以述说,现在是众志成城,合成一股绳,天地更阔机会也更多。
厂里给谢京福和黄玉斌都分派了几个徒弟,其中也有三四个女徒弟,也让他们和谢京福按照过去的传统签订了师徒合同,用传帮带的方式来提升大家的技艺。当时也有很多其他老作坊的师傅们跟着进来工作,谢京福得到父亲的叮咛,每走一步,要如履薄冰,不要稍微有些成绩,就得意忘形。于是,他常常与黄玉斌业余十分沟通交流,很快,两个人又有了新的默契。
一个午休时间,黄玉斌的徒弟小张孝敬了师傅一包双燕牌香烟,他抽了几口,想起有些事要找谢京福商量一下,就想趁着谢京福的空闲来找他一趟。他从自己的烧蓝车间跑到在掐丝车间里,远远地似乎看到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往一只大瓶子上贴纸。他认得那是谢京福的两个小徒弟丁辉与王小乐,做了许多年珐琅了,黄玉斌自然知道他们是在偷偷拓样子,不由摇头叹了口气。
不一会儿,他看到谢京福一边啃着一个冷馒头一边看一份图样,走了过来。他看到黄玉斌,招呼了一声,便拿起案头掉了一片漆的搪瓷缸喝了一口水,然后微微蹙了下眉,明显那水是冷的。
“福哥,你那下边的学徒工年纪轻轻,不好好学习基本功,有空闲倒是学会了偷师傅的样图来了。”
“我知道。这些胎体上到处都是黑墨汁,难道我还猜不透他们的心思?”
“你知道你还这样纵容他们?”
“这不是纵容,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了,师傅的手艺也没必要留个后手,他们有本事就全学了我才高兴。虽然他们想的是走捷径的法子,不是我们老一辈师傅教的脚踏实地,但是毕竟他们是肯花私心琢磨这些事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不是这个理儿么?对了,玉斌,你找我有什么事?”
黄玉斌看到私下无人,便低声说:“福哥,我这里有些好事,想和你说说,如果你觉得妥当,我们师兄弟就一起干。”
“哦?”
“前些日子,遇到以前在前门老烧蓝作坊里的一个兄弟老吴,他家祖上是清朝造办处珐琅作坊的,他早就不做这个行当了,他说这个行当费时费力,却比不得那些瓷器的价值,好手艺也是给浪费了,就跟着别人改做珐琅瓷了。他说现在虽然我们成了公私合营大厂的职工,有了固定工资,但是这年月缺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兄弟都还没娶妻呢!他还说现在国家安定,也开始注重手艺了。现下有个搞皮影戏的朋友,偷偷揽了点外贸的私活,需要找两个人帮忙做些皮影工艺品,他说我们这个行当一通百通,情急之下,叫咱们去帮忙,当然人家给一个人五百块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看,我们抽空是不是去看看?”
这话刚刚说完,谢京福的脸色骤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将手里的搪瓷缸重重放下,叹了口气:“玉斌,你师傅当年说过,做珐琅最忌讳的就是私心杂念,你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让他老人家知道还不知道有多痛心,外面的人怎么干,干什么,与我们何干?国家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你居然还有这个心思?要是你听我的,就什么都别想,专心做你的烧蓝师傅去!”
黄玉斌有些尴尬了,没有想到谢京福这样决绝,只好退缩了几步,“嘿嘿”笑着:“福哥,看你,一脸包黑子的样儿!我就是说说,这不什么都没干嘛!”
谢京福的口气这才软了下来:“玉斌,我们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固然有家传的手艺,但是现在的一切都在变,我们也得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有空不如我们再多想想怎么精进自己的手艺,也给徒弟们做个榜样。虽然你眼下在烧蓝车间,但是听说李厂长也看上了你的手艺,想让你也来掐丝车间,你有空还是要练习一下掰花,你看看你掰的牡丹花难看的要命,那鸟儿的身子比牡丹花还大,虽然是有点形色,但是就是少那么点儿美感,不知道缺了什么。”
黄玉斌开始苦笑起来,原本想自己过来讨个好的,没想到遭受到师兄这一顿数落,于是小声说:“福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这不是急嘛!我都老大不小了,我娘天天催着我早点儿娶媳妇,我这一穷二白的,也养不起媳妇呀!”
“那也不能胡思乱想,你这是翅膀还没长硬就想飞,这可是我们珐琅人的大忌。”
“是,福哥,工作时间到了,我这就回去了。”黄玉斌看到四周三三两两开始出现上工的人,头皮有些发紧,想赶紧溜走。
“回来,你刚才说那什么皮影戏,是从光下就看的清那人物的动作服饰线条?”
黄玉斌不太明白谢京福此刻的心思,只是应道:“那是,那些胳膊腿都有线条,灵动得很,样貌袍褂都清清楚楚的,那可是另外一门好匠心呢!”
谢京福看着远处的墙壁上,脸上的冰渐渐融化,嘴角出现了一种黄玉斌看不懂的微笑,他拿起一块铜丝,左边一掰,右边一掰,很快就掰成一朵菊花的样子,他喊着一个徒弟上前用手电筒对着墙壁照射着手里的铜丝菊花,众人在那片白色的墙壁上看到一个轮廓分明、有形有样的菊花花瓣。
他喊了一下:“拿纸笔。”很快就有人拿过来。他画下了这朵菊花,对着正观望的学徒工们说:“这些天我观摩了一些国画大师的作品,发现我们掰的菊花虽然周正,但是和那些国画里的菊花还是不同,国画里的菊花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写意深情,我琢磨着,这种感觉就艺术美感吧!大家看,我刚想到一个怎样让自己的作品更好看的办法,大家把看到的花草树木,通过投影的方法,来找寻那种自然美的艺术感,然后再照着投影将花儿画下来,再掐丝,时间久了,那种比例自然就掌握了……”
黄玉斌看到四周那些年轻的与年老的工匠们,都用仰望的眼光,凝视还在神采飞扬讲述着这种新创意的谢京福,感觉到自己的心情黯然起来。在谢京福的所在之处,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光彩,也许自己也要好好上进了。
“铜胎掐丝珐琅的特点就是全景设计,要上花,也要粘地,蓝没有这个地子抓着,就会崩,任何一步都不懈松懈。你们还年轻,不要总是想着干上手活,嫌下手活丢人。师傅们在粘龙,你们就得天天码龙鳞,这就是师徒之道。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掐丝珐琅,就是在绘画,我们以铜胎为纸,以铜丝勾线,以珐琅彩填色,在珐琅器上绘出永不变色的国画,大家说呢!”
谢京福说着,自己上前拿起手电筒,照着手里的一片铜丝,粗犷的笑容里忽然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黄玉斌转身回去的时候看了一眼,谢京福高大的身体笔直伫立在光影下,他的轮廓就这样映照在后边的墙壁上,把自己变成了皮影戏里的一个人。
他不敢相信,这个曾经一直在作坊里做粗使活的小珐琅匠变成了眼前这个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谢京福珍惜这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他从来没有休过礼拜天,有空就自己或带着几个徒弟去野外、去动物园采风观摩。珐琅的事业,需要一份美好的感觉,这种感觉需要再长期的生活中渐渐找寻,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替父辈们的事业,谢京福感觉到了饱满,也渐渐在这种与时光相伴的劳作中忘记了过去的痛。
谢京福看着自己已经做完的掐丝,还是觉得有一个小小的花瓣不够精致,看了看时间还早,于是屏住呼吸,轻轻按住那花瓣周围的铜丝,以防止它们连带掉落下来。把它轻轻拆了下来,又仔细一点点重新调整了几下,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当他把它完整地粘贴到铜胎上,他看到一个穿着中山服的人正微笑看着自己。他认识这个人,是入场时候就见过的,负责生产经营的李副厂长。
“你姓谢吧?是老北京城里鼎鼎大名的珐琅世家谢氏传人?”
谢京福站起身来,应了一声:“厂长您过誉了,不过就是家里传下来的是手艺活。做多了,自然就熟了。”
李副厂长握住了谢京福的手:“太好了,我看你这不用图纸就会掰花的技术,就知道你必定出身于老手艺人家,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样吧,你入场后直接跳过学徒工这个阶段,直接做带徒弟的匠师,工资也要比学徒工高一档。这样的人才,我们是大大欢迎呀!欢迎你们加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谢京福懵了,顿时觉的繁花满地,自己的心一点点暖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了一句:“为人民服务!”这句标语在街头小巷贴了很多,已经默默地记在自己心里,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句话居然和自己也扯上关系。
李副厂长又亲自拍着谢京福的肩膀说:“我们现在最需要你这样有经验的匠师带徒弟,你看看,还是年轻人多,他们还没能体会出这珐琅事业的艰辛,全靠师傅边教便带,当然还得教他们做人。我看到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就知道你的人品一定差不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四周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谢京福看着四周到处都是羡慕嫉妒的眼神,觉得胸腔里一股热流齐齐涌上,颤抖着说:“李厂长,我这水平恐怕还是欠缺。”
“安心做好你的传帮带师傅吧!厂里会支持你的。”
他郑重地看着李副厂长,还想推辞,却遭到了李厂长的决绝,无奈只好答应下来。
下班的时候,黄玉斌对谢京福说:“我说师兄,你走哪里都是星光灿烂呀!你一入场就当了师傅,工资还比别人高,我师傅可真是偏心,只把你教得这样出类拔萃,难道让我们这些师兄弟都去喝西北风?”
谢京福并不理睬他的胡搅蛮缠,只是狠狠朝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去你的!赶紧干正经事,你还不知道我家老爷子那人品?”
黄玉斌被打,不甘心地嚷着叫着,朝着前边奔跑谢京福追了过去。谢京福没有笑,想起父亲的话,做珐琅要心静,不要理睬别人的眼光,今后的生活更加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该何去何从。
谢京福也庆幸自己懂得父亲的一片苦心,珐琅厂卓越的资源也给了珐琅匠师们更多的滋养。谢京福以前与父亲是单打独斗,一番困难自是难以述说,现在是众志成城,合成一股绳,天地更阔机会也更多。
厂里给谢京福和黄玉斌都分派了几个徒弟,其中也有三四个女徒弟,也让他们和谢京福按照过去的传统签订了师徒合同,用传帮带的方式来提升大家的技艺。当时也有很多其他老作坊的师傅们跟着进来工作,谢京福得到父亲的叮咛,每走一步,要如履薄冰,不要稍微有些成绩,就得意忘形。于是,他常常与黄玉斌业余十分沟通交流,很快,两个人又有了新的默契。
一个午休时间,黄玉斌的徒弟小张孝敬了师傅一包双燕牌香烟,他抽了几口,想起有些事要找谢京福商量一下,就想趁着谢京福的空闲来找他一趟。他从自己的烧蓝车间跑到在掐丝车间里,远远地似乎看到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往一只大瓶子上贴纸。他认得那是谢京福的两个小徒弟丁辉与王小乐,做了许多年珐琅了,黄玉斌自然知道他们是在偷偷拓样子,不由摇头叹了口气。
不一会儿,他看到谢京福一边啃着一个冷馒头一边看一份图样,走了过来。他看到黄玉斌,招呼了一声,便拿起案头掉了一片漆的搪瓷缸喝了一口水,然后微微蹙了下眉,明显那水是冷的。
“福哥,你那下边的学徒工年纪轻轻,不好好学习基本功,有空闲倒是学会了偷师傅的样图来了。”
“我知道。这些胎体上到处都是黑墨汁,难道我还猜不透他们的心思?”
“你知道你还这样纵容他们?”
“这不是纵容,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了,师傅的手艺也没必要留个后手,他们有本事就全学了我才高兴。虽然他们想的是走捷径的法子,不是我们老一辈师傅教的脚踏实地,但是毕竟他们是肯花私心琢磨这些事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不是这个理儿么?对了,玉斌,你找我有什么事?”
黄玉斌看到私下无人,便低声说:“福哥,我这里有些好事,想和你说说,如果你觉得妥当,我们师兄弟就一起干。”
“哦?”
“前些日子,遇到以前在前门老烧蓝作坊里的一个兄弟老吴,他家祖上是清朝造办处珐琅作坊的,他早就不做这个行当了,他说这个行当费时费力,却比不得那些瓷器的价值,好手艺也是给浪费了,就跟着别人改做珐琅瓷了。他说现在虽然我们成了公私合营大厂的职工,有了固定工资,但是这年月缺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兄弟都还没娶妻呢!他还说现在国家安定,也开始注重手艺了。现下有个搞皮影戏的朋友,偷偷揽了点外贸的私活,需要找两个人帮忙做些皮影工艺品,他说我们这个行当一通百通,情急之下,叫咱们去帮忙,当然人家给一个人五百块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看,我们抽空是不是去看看?”
这话刚刚说完,谢京福的脸色骤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将手里的搪瓷缸重重放下,叹了口气:“玉斌,你师傅当年说过,做珐琅最忌讳的就是私心杂念,你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让他老人家知道还不知道有多痛心,外面的人怎么干,干什么,与我们何干?国家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你居然还有这个心思?要是你听我的,就什么都别想,专心做你的烧蓝师傅去!”
黄玉斌有些尴尬了,没有想到谢京福这样决绝,只好退缩了几步,“嘿嘿”笑着:“福哥,看你,一脸包黑子的样儿!我就是说说,这不什么都没干嘛!”
谢京福的口气这才软了下来:“玉斌,我们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固然有家传的手艺,但是现在的一切都在变,我们也得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有空不如我们再多想想怎么精进自己的手艺,也给徒弟们做个榜样。虽然你眼下在烧蓝车间,但是听说李厂长也看上了你的手艺,想让你也来掐丝车间,你有空还是要练习一下掰花,你看看你掰的牡丹花难看的要命,那鸟儿的身子比牡丹花还大,虽然是有点形色,但是就是少那么点儿美感,不知道缺了什么。”
黄玉斌开始苦笑起来,原本想自己过来讨个好的,没想到遭受到师兄这一顿数落,于是小声说:“福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这不是急嘛!我都老大不小了,我娘天天催着我早点儿娶媳妇,我这一穷二白的,也养不起媳妇呀!”
“那也不能胡思乱想,你这是翅膀还没长硬就想飞,这可是我们珐琅人的大忌。”
“是,福哥,工作时间到了,我这就回去了。”黄玉斌看到四周三三两两开始出现上工的人,头皮有些发紧,想赶紧溜走。
“回来,你刚才说那什么皮影戏,是从光下就看的清那人物的动作服饰线条?”
黄玉斌不太明白谢京福此刻的心思,只是应道:“那是,那些胳膊腿都有线条,灵动得很,样貌袍褂都清清楚楚的,那可是另外一门好匠心呢!”
谢京福看着远处的墙壁上,脸上的冰渐渐融化,嘴角出现了一种黄玉斌看不懂的微笑,他拿起一块铜丝,左边一掰,右边一掰,很快就掰成一朵菊花的样子,他喊着一个徒弟上前用手电筒对着墙壁照射着手里的铜丝菊花,众人在那片白色的墙壁上看到一个轮廓分明、有形有样的菊花花瓣。
他喊了一下:“拿纸笔。”很快就有人拿过来。他画下了这朵菊花,对着正观望的学徒工们说:“这些天我观摩了一些国画大师的作品,发现我们掰的菊花虽然周正,但是和那些国画里的菊花还是不同,国画里的菊花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写意深情,我琢磨着,这种感觉就艺术美感吧!大家看,我刚想到一个怎样让自己的作品更好看的办法,大家把看到的花草树木,通过投影的方法,来找寻那种自然美的艺术感,然后再照着投影将花儿画下来,再掐丝,时间久了,那种比例自然就掌握了……”
黄玉斌看到四周那些年轻的与年老的工匠们,都用仰望的眼光,凝视还在神采飞扬讲述着这种新创意的谢京福,感觉到自己的心情黯然起来。在谢京福的所在之处,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光彩,也许自己也要好好上进了。
“铜胎掐丝珐琅的特点就是全景设计,要上花,也要粘地,蓝没有这个地子抓着,就会崩,任何一步都不懈松懈。你们还年轻,不要总是想着干上手活,嫌下手活丢人。师傅们在粘龙,你们就得天天码龙鳞,这就是师徒之道。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掐丝珐琅,就是在绘画,我们以铜胎为纸,以铜丝勾线,以珐琅彩填色,在珐琅器上绘出永不变色的国画,大家说呢!”
谢京福说着,自己上前拿起手电筒,照着手里的一片铜丝,粗犷的笑容里忽然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黄玉斌转身回去的时候看了一眼,谢京福高大的身体笔直伫立在光影下,他的轮廓就这样映照在后边的墙壁上,把自己变成了皮影戏里的一个人。
他不敢相信,这个曾经一直在作坊里做粗使活的小珐琅匠变成了眼前这个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谢京福珍惜这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他从来没有休过礼拜天,有空就自己或带着几个徒弟去野外、去动物园采风观摩。珐琅的事业,需要一份美好的感觉,这种感觉需要再长期的生活中渐渐找寻,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替父辈们的事业,谢京福感觉到了饱满,也渐渐在这种与时光相伴的劳作中忘记了过去的痛。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