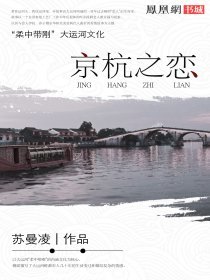第十二章 夙愿得偿2
时光飞逝,转眼已经是来年的六月。
谢慎今天早上趁着空气新鲜,他独自一个人到了街心花园溜达。风是暖的,花是艳的,有几个七八岁的孩子一边吹着泡泡糖,一面跳着方格子。他坐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那些可爱的笑脸,久违的亲切感与期盼又回来了。他渴望看到谢家的后代早点降临,但是这个不解风情的儿子就这样蹉跎了岁月,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好姻缘。他也知道自己儿子不是那种得陇望蜀的人,而是只有一根筋,他若不愿意,就是十匹马也拉不回来。
家里已经被那个伊杭和她的儿子给占满了,儿子的心也被占满了。谢慎的这种孤独感,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有的体验,但是谢慎自己并不讨厌伊杭,只是不习惯、也不能接受这个以前的主人居然成了儿子的女人,这种滋味,让他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他觉得不舒服。而且,这个女人只是空有个高贵的身份,并不是冰清玉洁的好姑娘,她一个人栖身在谢家还不够,还带着个拖油瓶。谢家的门第虽然不高,但是要的是清白,可是儿子和那个伊杭已经把这些都彻底践踏了。
回来的时候,正看到儿子谢京福和伊杭两个人一起逗弄华华其乐融融的场景,他心中有些不太高兴。
他一进屋,就听到伊杭说:“谢叔叔,您吃了吗?锅里还有热的饭菜。”
伊杭自从进了这个院子,对谢慎极其谨慎尊重,将谢慎当做长辈对待,不曾有一丝一毫地懈怠。这一切让谢慎每次听着,都有着恍如梦中的感觉。伊杭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也是向自己示好,但是谢慎还是有些不高兴,他甚至希望,这个傅伊杭从来都不曾出现过。唯一的儿子把半辈子的心都用在她们母子的身上了,他的心又怎么能不失落?
于是,他扯着嗓子回道:“我吃过了,今天有个阔气的老朋友在外边请客,省了自己家的饭菜,不然我们家这么多口人,那点粮食怎么够吃?咱们这个月的口粮又快没了吧?”
“口粮都领回来了,爹,咱家现在不是还有粮食吗?”
谢慎白了儿子一眼,说:“现在刚刚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就不知道节省了?虽然你是个国营厂的职工,但是本来我们也不富裕,现在买什么都得要‘票’,得算计着过日子。我这辈子真是命苦,临到老了,还要成天操心这些柴米油盐的事情,这儿子是白养了!”
谢京福听了这话,敏感地看了伊杭一样。伊杭是个骨子里都要强的女人,这些话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谢京福怕她承受不了。
但是,他看到伊杭并不在意,只是继续做着手里的事儿,声音传过来却很清楚:“谢叔叔,我看到那些郊区的农民都带着自己家的土特产来城里卖了,说明他们最难的时候也过去了。现在没有大户小户了,都是国家公民。口粮虽然不多,我已经在屋子后边的空地上种了些蔬菜瓜果,华华还小,我们省着点,再有这些时令蔬菜搭着,也就差不多了。等华华大了,我让他好好回报谢家的大恩大德。”
谢京福看到父亲张着嘴,很久没有说话,明显是伊杭这些话给震慑了。从小就为贵族世家服务的父亲,忽然被一个满族格格接连这样称呼,有些不能适应也是正常。
谢京福已经发现,伊杭真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满怀幻想且清高到骨子里的格格了,她的口中也早已经没有了“额娘”与“阿玛”的称呼了,她是将自己真正融入到新中国最普通民众的一员中去了。他为这样的伊杭感到骄傲,心里也就更加珍惜她了。
他转身想抱着华华出去玩,却看到小家伙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个盒子,用手指抠着,然后又用牙咬咬,小眉头皱着,试图想破解那盒子的秘密。
伊杭嗔怪地说:“看你,一个不留神就又要做坏事了,让妈妈看看你拿的什么?”
那盒子都有些生锈了,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它。伊杭也开始好奇了,那铁盒子还包着锦缎,锦缎里还有一个精致的小珐琅盒子。打开那盒子,蓝色的粉末就忽然飘散些在空中,还有些轻轻溅落在地上。
伊杭用手指摸了些,闻了闻,眼神忽然变成了一道闪电,迅速扫向谢京福,谢京福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这颜料的事,已经好几年了,这颜料果然是上等的好东西,一点儿都没有发生质变。
他以为伊杭会询问关于这东西的事儿,但是她只是将那盒子重新盖上,然后抱起华华说:“华华,你折腾了一天了,该洗澡睡了,明天妈妈再带你出去玩。”
谢京福看到父亲折腾了一天也是疲惫不堪,对父亲说:“走吧,让儿子给你老人家也洗个澡。”父亲没有拒绝,他便跟着父亲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谢慎看到谢京福进来,示意他关上门。然后自己低头叹了口气,说道:“今天我去见了几个老朋友,还有一个满人,他认识一个萨满法师,我就跟着去问了一下你们两个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宜?”
谢京福有些不满,说:“您也知道,我从来不信什么法师巫师的,这些都是没有影子的事,为什么还非要给自己上个枷锁呢?”
谢慎摇头:“这些说道虽然看似没有章法,但是流传到至今,还是有些智慧在里头的,不由你不信。你和伊杭的八字不合,是不会配成夫妻的,还是早点了断好。”
谢京福拿起已经浸泡得热乎乎的毛巾,一边给父亲擦背,一边说:“您老就不要说了。如果说珐琅的事儿,我就听会儿,如果是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就算了。”
谢慎的叹息声渐渐沉重起来:“我就知道,说了你也白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谢京福有些警惕性地看着老谋深算的父亲,下意识已经开始抵抗了。
“后儿上午九点,你拿着这个,到公主坟附近的福升饭店去一趟。”
谢京福看到,这是一个古旧的信封,拿起来轻飘飘的,不像是什么贵重东西,后天正好是周末,也有空,便应了一声。
洗完澡,谢慎只说了一句:“你记住,我是你亲爹,不会害你。”
“亲爹也得讲人情道理,反正你儿子不愿意的事,你是甭想。”说完,谢京福打开房间的门,把父亲换下来的脏衣服都泡在盆里,端着离开了,给父亲留了一个倔强的背影。
谢慎终于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想再来硬的。这封信里有重要的东西,在自己手里压了很多天,已然成为自己的心病。儿子终究是善良的,不会真心想忤逆父亲,而是放不下自己的心病。
谢慎自己也是这样,有一种病,一旦患了,就是一辈子都好不了。得了这病,会遍体鳞伤,甚至愿意舍了自己的一切,他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
还在他小时候,在皇宫里做了一辈子珐琅的祖父说过,当个一流的珐琅师傅,就不能被一个女子所困扰,女子可以娶回家来生儿育女,但是不能太过用心,一旦分心,就失去成为出类拔萃的大匠师的资本了。这层道理,谢慎到今天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如此平庸的缘故,就是因为在自己心里都不曾注意的角落,始终藏着一个女人。
所以,他此生,注定失败。
次日,谢京福到了厂里,发现自己有些心神不宁,他知道自己其实是被父亲的话影响了。他心中一直藏着一个女人的身影,他很贪恋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也是他自小缺少的。也许,人就是这样,缺什么想什么。他有时会暗笑,他思念了多年的伊杭,居然就这样奇迹般地重新走入自己的生命里。他甚至还想过,也许,有一天,她厌倦了这平淡的日子,会忽然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但是,他摇头,现在的伊杭毕竟不是以前的贵族格格了,她有着缜密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她知道她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应该相信她。但是,母亲这样一个字眼,对于自己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身份,他反倒不敢想了。他正思虑着,听到门响了起来,以为是自己的徒弟们来找自己去开会讨论设计图,便应了一声。
但是,门开了,出现的却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胖小伙子。这小伙子的嗓门很大,眉头很粗,身材也健壮得很,和刘天乐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样。
他走进来对着谢京福说:“谢伯伯,我是刘海猛,我爸是刘天乐。”
谢京福看到这个孩子,忽然想起“虎父无犬子”这句话来,这个孩子遗传了刘天乐的鼻子和眉峰,可是眼睛里一汪深不可测的黑泉水,与刘天乐的洒脱有很大不同。
他一点儿都不拘束,大大方方地说:“谢大爷,我想求您点事儿。”
“哦?”
“我爸昨天把我打了一顿,他是拿着那种扫大街用的笤帚疙瘩打的,您看,”刘海猛伸出胳膊让谢京福看上边的血瘀,“不光这样,他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我,满大街喊着,说要挖个坑把我埋了,嫌我丢了他的人。”
“你爸什么时候成了法西斯了?他凭什么打你埋你?”
“我爸那脾气,您还不知道。他成天和别人乐乐呵呵,就是一看到我就绷着脸。其实也没多大事,就是这个学期我的数学考试没及格,还有就是我上晚自习的时候带着同学们去游泳了,班主任和教导主任都生气了,说要停我的课。”
谢京福听得啼笑皆非,这一对父子冤家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都是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的不好。
他笑着说:“既然知道你爸的脾气,你还不顺着他?”
刘海猛摇头:“反正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他还说以后我再不好好学习,就让我以后跟着您学做珐琅。”
谢京福听得有些郁闷了,原来在刘天乐的眼里,这做珐琅无异于是一件最没出息的选择。
“总之,我是不会学的。万一我爸和您提起这个,您可一定得拒绝他!回头我请您吃饭。”
谢京福笑道:“请我吃饭?”
刘海猛郑重地点头:“我妈说,自从我爸到了珐琅厂,我就没有爸爸了。还说自从跟上您,就没有家了,以后我可不能像我爸那样连个家都回不了。”
谢京福无可奈何点头,没想到自己对刘天乐有这样巨大的影响力,只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原来家里人也是这样不喜欢做珐琅的丈夫与父亲,还有自己这个负责传帮带的师傅。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当游泳教练或者去开飞机,自由自在……”刘海猛郑重的神态使得谢京福都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他也重重点头,一口答应:“好,孩子,我答应你,不会勉强你学做珐琅,好吗?”
刘海猛朝谢京福深深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您。我就不耽搁您的时间了,我得赶紧回去,不能让我爸知道我来过,和您说过这些,求您了。”
谢京福连连点头:“好,我答应。”
看着这孩子如获重释般地离开了这里,谢京福忽然发现,自己确实该好好考虑这传承的事儿。过去谢家是代代父子相传,但现在国营的珐琅厂,也是需要有人要系统地想一想这些事了,他决定向厂里打报告,多花些时间长考虑下这个问题。
谢慎今天早上趁着空气新鲜,他独自一个人到了街心花园溜达。风是暖的,花是艳的,有几个七八岁的孩子一边吹着泡泡糖,一面跳着方格子。他坐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那些可爱的笑脸,久违的亲切感与期盼又回来了。他渴望看到谢家的后代早点降临,但是这个不解风情的儿子就这样蹉跎了岁月,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好姻缘。他也知道自己儿子不是那种得陇望蜀的人,而是只有一根筋,他若不愿意,就是十匹马也拉不回来。
家里已经被那个伊杭和她的儿子给占满了,儿子的心也被占满了。谢慎的这种孤独感,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有的体验,但是谢慎自己并不讨厌伊杭,只是不习惯、也不能接受这个以前的主人居然成了儿子的女人,这种滋味,让他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他觉得不舒服。而且,这个女人只是空有个高贵的身份,并不是冰清玉洁的好姑娘,她一个人栖身在谢家还不够,还带着个拖油瓶。谢家的门第虽然不高,但是要的是清白,可是儿子和那个伊杭已经把这些都彻底践踏了。
回来的时候,正看到儿子谢京福和伊杭两个人一起逗弄华华其乐融融的场景,他心中有些不太高兴。
他一进屋,就听到伊杭说:“谢叔叔,您吃了吗?锅里还有热的饭菜。”
伊杭自从进了这个院子,对谢慎极其谨慎尊重,将谢慎当做长辈对待,不曾有一丝一毫地懈怠。这一切让谢慎每次听着,都有着恍如梦中的感觉。伊杭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也是向自己示好,但是谢慎还是有些不高兴,他甚至希望,这个傅伊杭从来都不曾出现过。唯一的儿子把半辈子的心都用在她们母子的身上了,他的心又怎么能不失落?
于是,他扯着嗓子回道:“我吃过了,今天有个阔气的老朋友在外边请客,省了自己家的饭菜,不然我们家这么多口人,那点粮食怎么够吃?咱们这个月的口粮又快没了吧?”
“口粮都领回来了,爹,咱家现在不是还有粮食吗?”
谢慎白了儿子一眼,说:“现在刚刚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就不知道节省了?虽然你是个国营厂的职工,但是本来我们也不富裕,现在买什么都得要‘票’,得算计着过日子。我这辈子真是命苦,临到老了,还要成天操心这些柴米油盐的事情,这儿子是白养了!”
谢京福听了这话,敏感地看了伊杭一样。伊杭是个骨子里都要强的女人,这些话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谢京福怕她承受不了。
但是,他看到伊杭并不在意,只是继续做着手里的事儿,声音传过来却很清楚:“谢叔叔,我看到那些郊区的农民都带着自己家的土特产来城里卖了,说明他们最难的时候也过去了。现在没有大户小户了,都是国家公民。口粮虽然不多,我已经在屋子后边的空地上种了些蔬菜瓜果,华华还小,我们省着点,再有这些时令蔬菜搭着,也就差不多了。等华华大了,我让他好好回报谢家的大恩大德。”
谢京福看到父亲张着嘴,很久没有说话,明显是伊杭这些话给震慑了。从小就为贵族世家服务的父亲,忽然被一个满族格格接连这样称呼,有些不能适应也是正常。
谢京福已经发现,伊杭真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满怀幻想且清高到骨子里的格格了,她的口中也早已经没有了“额娘”与“阿玛”的称呼了,她是将自己真正融入到新中国最普通民众的一员中去了。他为这样的伊杭感到骄傲,心里也就更加珍惜她了。
他转身想抱着华华出去玩,却看到小家伙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个盒子,用手指抠着,然后又用牙咬咬,小眉头皱着,试图想破解那盒子的秘密。
伊杭嗔怪地说:“看你,一个不留神就又要做坏事了,让妈妈看看你拿的什么?”
那盒子都有些生锈了,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它。伊杭也开始好奇了,那铁盒子还包着锦缎,锦缎里还有一个精致的小珐琅盒子。打开那盒子,蓝色的粉末就忽然飘散些在空中,还有些轻轻溅落在地上。
伊杭用手指摸了些,闻了闻,眼神忽然变成了一道闪电,迅速扫向谢京福,谢京福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这颜料的事,已经好几年了,这颜料果然是上等的好东西,一点儿都没有发生质变。
他以为伊杭会询问关于这东西的事儿,但是她只是将那盒子重新盖上,然后抱起华华说:“华华,你折腾了一天了,该洗澡睡了,明天妈妈再带你出去玩。”
谢京福看到父亲折腾了一天也是疲惫不堪,对父亲说:“走吧,让儿子给你老人家也洗个澡。”父亲没有拒绝,他便跟着父亲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谢慎看到谢京福进来,示意他关上门。然后自己低头叹了口气,说道:“今天我去见了几个老朋友,还有一个满人,他认识一个萨满法师,我就跟着去问了一下你们两个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宜?”
谢京福有些不满,说:“您也知道,我从来不信什么法师巫师的,这些都是没有影子的事,为什么还非要给自己上个枷锁呢?”
谢慎摇头:“这些说道虽然看似没有章法,但是流传到至今,还是有些智慧在里头的,不由你不信。你和伊杭的八字不合,是不会配成夫妻的,还是早点了断好。”
谢京福拿起已经浸泡得热乎乎的毛巾,一边给父亲擦背,一边说:“您老就不要说了。如果说珐琅的事儿,我就听会儿,如果是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就算了。”
谢慎的叹息声渐渐沉重起来:“我就知道,说了你也白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谢京福有些警惕性地看着老谋深算的父亲,下意识已经开始抵抗了。
“后儿上午九点,你拿着这个,到公主坟附近的福升饭店去一趟。”
谢京福看到,这是一个古旧的信封,拿起来轻飘飘的,不像是什么贵重东西,后天正好是周末,也有空,便应了一声。
洗完澡,谢慎只说了一句:“你记住,我是你亲爹,不会害你。”
“亲爹也得讲人情道理,反正你儿子不愿意的事,你是甭想。”说完,谢京福打开房间的门,把父亲换下来的脏衣服都泡在盆里,端着离开了,给父亲留了一个倔强的背影。
谢慎终于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想再来硬的。这封信里有重要的东西,在自己手里压了很多天,已然成为自己的心病。儿子终究是善良的,不会真心想忤逆父亲,而是放不下自己的心病。
谢慎自己也是这样,有一种病,一旦患了,就是一辈子都好不了。得了这病,会遍体鳞伤,甚至愿意舍了自己的一切,他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
还在他小时候,在皇宫里做了一辈子珐琅的祖父说过,当个一流的珐琅师傅,就不能被一个女子所困扰,女子可以娶回家来生儿育女,但是不能太过用心,一旦分心,就失去成为出类拔萃的大匠师的资本了。这层道理,谢慎到今天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如此平庸的缘故,就是因为在自己心里都不曾注意的角落,始终藏着一个女人。
所以,他此生,注定失败。
次日,谢京福到了厂里,发现自己有些心神不宁,他知道自己其实是被父亲的话影响了。他心中一直藏着一个女人的身影,他很贪恋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也是他自小缺少的。也许,人就是这样,缺什么想什么。他有时会暗笑,他思念了多年的伊杭,居然就这样奇迹般地重新走入自己的生命里。他甚至还想过,也许,有一天,她厌倦了这平淡的日子,会忽然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但是,他摇头,现在的伊杭毕竟不是以前的贵族格格了,她有着缜密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她知道她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应该相信她。但是,母亲这样一个字眼,对于自己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身份,他反倒不敢想了。他正思虑着,听到门响了起来,以为是自己的徒弟们来找自己去开会讨论设计图,便应了一声。
但是,门开了,出现的却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胖小伙子。这小伙子的嗓门很大,眉头很粗,身材也健壮得很,和刘天乐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样。
他走进来对着谢京福说:“谢伯伯,我是刘海猛,我爸是刘天乐。”
谢京福看到这个孩子,忽然想起“虎父无犬子”这句话来,这个孩子遗传了刘天乐的鼻子和眉峰,可是眼睛里一汪深不可测的黑泉水,与刘天乐的洒脱有很大不同。
他一点儿都不拘束,大大方方地说:“谢大爷,我想求您点事儿。”
“哦?”
“我爸昨天把我打了一顿,他是拿着那种扫大街用的笤帚疙瘩打的,您看,”刘海猛伸出胳膊让谢京福看上边的血瘀,“不光这样,他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我,满大街喊着,说要挖个坑把我埋了,嫌我丢了他的人。”
“你爸什么时候成了法西斯了?他凭什么打你埋你?”
“我爸那脾气,您还不知道。他成天和别人乐乐呵呵,就是一看到我就绷着脸。其实也没多大事,就是这个学期我的数学考试没及格,还有就是我上晚自习的时候带着同学们去游泳了,班主任和教导主任都生气了,说要停我的课。”
谢京福听得啼笑皆非,这一对父子冤家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都是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的不好。
他笑着说:“既然知道你爸的脾气,你还不顺着他?”
刘海猛摇头:“反正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他还说以后我再不好好学习,就让我以后跟着您学做珐琅。”
谢京福听得有些郁闷了,原来在刘天乐的眼里,这做珐琅无异于是一件最没出息的选择。
“总之,我是不会学的。万一我爸和您提起这个,您可一定得拒绝他!回头我请您吃饭。”
谢京福笑道:“请我吃饭?”
刘海猛郑重地点头:“我妈说,自从我爸到了珐琅厂,我就没有爸爸了。还说自从跟上您,就没有家了,以后我可不能像我爸那样连个家都回不了。”
谢京福无可奈何点头,没想到自己对刘天乐有这样巨大的影响力,只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原来家里人也是这样不喜欢做珐琅的丈夫与父亲,还有自己这个负责传帮带的师傅。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当游泳教练或者去开飞机,自由自在……”刘海猛郑重的神态使得谢京福都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他也重重点头,一口答应:“好,孩子,我答应你,不会勉强你学做珐琅,好吗?”
刘海猛朝谢京福深深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您。我就不耽搁您的时间了,我得赶紧回去,不能让我爸知道我来过,和您说过这些,求您了。”
谢京福连连点头:“好,我答应。”
看着这孩子如获重释般地离开了这里,谢京福忽然发现,自己确实该好好考虑这传承的事儿。过去谢家是代代父子相传,但现在国营的珐琅厂,也是需要有人要系统地想一想这些事了,他决定向厂里打报告,多花些时间长考虑下这个问题。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