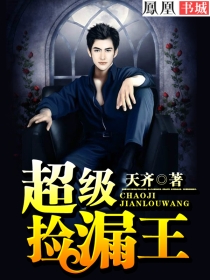第3章 河底竖棺
发送了祖母之后,家里也就只剩下三十亩地,一辆大车,和一些字画了。
刚好也就是这时候,政府开始给划成分,我家被划成了富农。成了贫下中农可以团结的对象。
我家里的财产拉了三大车,都拉到了公社充公了。
就算是这样,由于陈俊儒勤快,头脑灵活,日子还是过得比别家要好。
有一年腊月,下了一场没膝盖的大雪。陈俊儒从外面用大骡子车拉回来一个姑娘,直接就塞到我爹炕上了。这姑娘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是被我姥姥从河南一路要饭带到这里的,眼看就要冻死饿死了,陈俊儒看到之后,就把我母亲带回来了。
隔年我母亲就生了我,生我的那年刚好原子弹爆炸,举国欢腾。所以陈俊儒给我起名字叫了个陈原。
后来我问为啥没叫陈原子,他说听我祖母说过,一个字的名字高贵,古代人名字都是一个字的,比如刘备,关羽,张飞啥的。
我爹是看不上我母亲的,他一直嫌弃她没有文化,叫花子出身,一个大字不识,不懂礼数。慢慢的我爹就开始对母亲冷暴力。
我爹在家一天啥也不干,除了赌钱喝酒就是听戏,要么就是找东刁老郭家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乱搞。
按照辈分,那女人还是我爹的堂姨,也就是我祖母的一个堂妹。这事儿搞得风言风语不成体统。
有一次,我爹被陈俊儒从那女人的被窝里抓回来狠狠打了一顿,他一赌气偷了家里私藏的一袋子大洋给了他的相好儿老姨,然后离家出走了。
后来我爹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是自己去参军了。
再后来死在了老山前线成了烈士,军队派人送回来一个骨灰盒和一个军功章。
那时候我都十几岁了。
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才十六岁,守寡的时候也就是三十来岁。陈俊儒知道留也留不住。
现在我母亲在我家养的又白又胖,水水灵灵小寡妇,惦记的人太多,整天来招来野男人串门子。一来二去搞得门风很不好。
陈俊儒管也管不了,经常和我母亲吵架,陈俊儒一想,干脆就把我母亲送去了唐山市区的表舅爷那里,舅爷给我母亲找了个铁路工人,就这么嫁了。
那铁路工人给了陈俊儒一笔彩礼,就再也没联系了。
从我记事起,陈俊儒都会在天不亮的时候背着粪箕子出去。
用他的话说就是:庄稼佬,往前奔,不拾柴火就拣粪。他总是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回来,那时候粪箕子已经满了。
在我十五岁的那年春天,陈俊儒背着粪箕子出去了,是被人用停放死人的排子抬回来的。
他从那天开始就疯疯癫癫,过了几天后终于清醒了过来。
他说那天出去之后,有个当兵的飞行员说带他坐飞机去找他儿子。他就跟着这个飞行员上了飞机,这飞机起飞之后一直就那么飞,越飞越高,后来看地面上的房子就像是火柴盒那么大了。
总这么飞也不到地方,他就问飞行员,啥时候能看到他儿子,飞行员不耐烦了,说耐心等着,很快就到了。
陈俊儒一直追问,这飞行员竟然打开了飞机的舱门,撇下飞机自己跳下去了。这时候陈俊儒慌了,他没有开过飞机,但是他赶过骡子车,干脆就上去把飞机当骡子车赶着走,想往前走就喊“驾”,左转弯就是“咿”,右转弯就是“喔”。
开始的时候这飞机还听使唤,后来这飞机就惊了,开始乱飞,在空中把陈俊儒转得头晕,陈俊儒很快就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家里的炕上。
实际上,村里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坐在坟地里的死人排子上,在胡言乱语。
这件事之后,陈俊儒的身体就不行了,我表舅找了一个东北看香的给看看,说陈俊儒是招了狐仙了,不过这狐仙不是来害陈俊儒的,没有坏心。
接下来,陈俊儒就开始信佛,信道,信萨满,家里就没有断了来做法事的。后来陈俊儒总结出来一整套关于灵异方面的东西,干脆就谁也不信了,开始信自己。
陈俊儒最后在这个世上的半年里,一直活得浑浑噩噩,给我讲了很多他的往事,尤其是反反复复讲他和祖母的婚事,讲那天晚上看到的两个老鬼。
他甚至记得那间大院子的任何细节,尤其是说起那些金子的时候,两眼会像金子一样放光。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到了晚上,陈俊儒就会在屋子里和人谈话,我在对屋不想听都能听到,从前到后总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但是有来有回,挺渗人的。村里亲戚告诉我,陈俊儒撞克我祖母了,他这是在和我祖母聊天。
后来,陈俊儒砍了后院的一棵花椒树,弄了个树杈,自己在这树杈上糊了个纸人,还买了假发戴在纸人头上。
每天就用那把乌木梳子给纸人梳头。晚上总是不睡觉,一说就能说一晚上。
接下来的一个月不吃东西,脖子里肿了一个疙瘩,喝水都费劲了,在炕上熬了一个月,没拉也没尿,干干净净死在了我家的热炕上。
我整理遗物的时候,也就没啥值钱的东西了。留下来的两件东西就是那把梳子和那本《地理万山图》。
这《地理万山图》我从不认字的时候就开始翻着看里面的图画。认识字了就开始看里面晦涩难懂的一些古文。
说心里话,那时候我是看得迷迷糊糊,一直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本风水书。
我一般大的小伙伴儿有的去当兵了,有的去上学了。我必须养活自己,勉强上完了初中,然后跟着生产队去修河去了。
我和王虎就是在修河的时候认识的。
王虎是北京人,小名虎子。他成分不好,是个资本家的家庭。家里人为了让王虎有个好前程,就把王虎过继给了滦县的贫农舅舅家,户口这么迁过来,这王虎就也成了光荣的贫农了。
王虎那时候还小,后来逐渐长大了才发现,贫农又有些不吃香了,现在大家又开始追捧万元户了。
修河的时候,我和虎子是一个担子,我俩一前一后抬大筐,从河底往河岸上抬河沙,肩膀都压得红·肿出血,就为了挣那一天块八毛的工资。
一来二去,我和王虎就熟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王虎就抱怨说:“你说我冤不冤,当年要是不把我过继到农村,现在我在京城也分房子了。
我家平反了,按照户口分了房子,哥哥姐姐也都找到了工作,有的当了教师,有的成了工人。就剩我一个在这里修河,我比窦娥都冤。”
我说:“我是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这觉悟就有问题了。”
王虎说:“我觉得我适合当兵保卫祖国,站在祖国的边疆,为人民站好每一班岗。或者我可以当个火车司机,凭什么我就在这里修河啊!修河的人这么多,不差我一个,我更适合有挑战性的岗位。我这颗滚烫的红心在燃烧,你懂么?我急切地想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你懂么?!”
我笑着说:“你就再把户口调回去呗。”
“调动户口哪里那么容易,当初过继给舅舅,可是通过革委会办理的正规手续。城市户口转农村户口容易,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想都别想。我从资本家到了贫农,这才高兴几年啊,现在风向又变了,资本家又吃香了。我想变回去怎么就不行了?谁能给我主持公道!”
说着,王虎愤怒地把铁锹往河底一戳,这一下没戳进去,就听到当的一声响。
我和王虎都愣了一下,王虎用铁锹扒拉了两下,在这河底竟然出现了一块紫黑色的木板。
王虎和我都好奇,开始用铁锹铲去上面的河沙,想不到这木板越清理越大,最后竟然清理出来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
王虎左右看看,小声说:“老陈,别吱声。”
说着就开始埋,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干啥,不过看王虎的样子似乎有什么秘密。埋完了之后,王虎一搂我的肩膀,趴在我耳边小声说:“老陈,别声张。”
“这箱子里有啥啊?挖出来打开看看呀!”我好奇地说。
王虎小声说:“这是一口棺材。”
我想了一下,心说不对啊。我说:“不会,棺材不会这么小。”
“竖着呢,这是发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王虎小声说,“我看了,这棺材是上好的乌木打造,上了九层漆,上面还有花鸟的纹路,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奶奶,搞不好是个清朝格格的棺材。里面肯定有货。”
我半信半疑地说:“不能吧。”
刚好这时候队长过来了,问我俩不干活嘀嘀咕咕干啥呢。
王虎顿时捂着说肚子疼,实在憋不住了,让我拎着棉大衣给他挡着,他这时候解开了裤子,蹲在这里拉了一泡屎。
不远处的大姑娘都躲得远远的,有已婚妇女开始骂他,用土坷垃砸他。
不过这个办法奏效,一直到天黑,也没有人来我和王虎的分段,安全地守护住了这口棺材的秘密。
我们的住宿地点在三里外的大龙沟,干一天活我倒下就睡着了。
我睡得正香,就梦到有一双爪子伸过来抓住了我的脑袋,我吓得一激灵,猛地睁开眼。这时候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说:“老陈,是我,虎子。”
我坐起来,围着棉被小声骂道:“你他妈有病吧,大晚上的不睡觉,你干啥啊!”
“起来,跟我走。”虎子用手电筒给我照着炕上的衣服,顺手把毛衣扔给了我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老陈,今晚过后,也许我俩就发了。快穿上毛衣,哎呦卧槽,你毛衣穿反了……”
刚好也就是这时候,政府开始给划成分,我家被划成了富农。成了贫下中农可以团结的对象。
我家里的财产拉了三大车,都拉到了公社充公了。
就算是这样,由于陈俊儒勤快,头脑灵活,日子还是过得比别家要好。
有一年腊月,下了一场没膝盖的大雪。陈俊儒从外面用大骡子车拉回来一个姑娘,直接就塞到我爹炕上了。这姑娘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是被我姥姥从河南一路要饭带到这里的,眼看就要冻死饿死了,陈俊儒看到之后,就把我母亲带回来了。
隔年我母亲就生了我,生我的那年刚好原子弹爆炸,举国欢腾。所以陈俊儒给我起名字叫了个陈原。
后来我问为啥没叫陈原子,他说听我祖母说过,一个字的名字高贵,古代人名字都是一个字的,比如刘备,关羽,张飞啥的。
我爹是看不上我母亲的,他一直嫌弃她没有文化,叫花子出身,一个大字不识,不懂礼数。慢慢的我爹就开始对母亲冷暴力。
我爹在家一天啥也不干,除了赌钱喝酒就是听戏,要么就是找东刁老郭家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乱搞。
按照辈分,那女人还是我爹的堂姨,也就是我祖母的一个堂妹。这事儿搞得风言风语不成体统。
有一次,我爹被陈俊儒从那女人的被窝里抓回来狠狠打了一顿,他一赌气偷了家里私藏的一袋子大洋给了他的相好儿老姨,然后离家出走了。
后来我爹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是自己去参军了。
再后来死在了老山前线成了烈士,军队派人送回来一个骨灰盒和一个军功章。
那时候我都十几岁了。
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才十六岁,守寡的时候也就是三十来岁。陈俊儒知道留也留不住。
现在我母亲在我家养的又白又胖,水水灵灵小寡妇,惦记的人太多,整天来招来野男人串门子。一来二去搞得门风很不好。
陈俊儒管也管不了,经常和我母亲吵架,陈俊儒一想,干脆就把我母亲送去了唐山市区的表舅爷那里,舅爷给我母亲找了个铁路工人,就这么嫁了。
那铁路工人给了陈俊儒一笔彩礼,就再也没联系了。
从我记事起,陈俊儒都会在天不亮的时候背着粪箕子出去。
用他的话说就是:庄稼佬,往前奔,不拾柴火就拣粪。他总是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回来,那时候粪箕子已经满了。
在我十五岁的那年春天,陈俊儒背着粪箕子出去了,是被人用停放死人的排子抬回来的。
他从那天开始就疯疯癫癫,过了几天后终于清醒了过来。
他说那天出去之后,有个当兵的飞行员说带他坐飞机去找他儿子。他就跟着这个飞行员上了飞机,这飞机起飞之后一直就那么飞,越飞越高,后来看地面上的房子就像是火柴盒那么大了。
总这么飞也不到地方,他就问飞行员,啥时候能看到他儿子,飞行员不耐烦了,说耐心等着,很快就到了。
陈俊儒一直追问,这飞行员竟然打开了飞机的舱门,撇下飞机自己跳下去了。这时候陈俊儒慌了,他没有开过飞机,但是他赶过骡子车,干脆就上去把飞机当骡子车赶着走,想往前走就喊“驾”,左转弯就是“咿”,右转弯就是“喔”。
开始的时候这飞机还听使唤,后来这飞机就惊了,开始乱飞,在空中把陈俊儒转得头晕,陈俊儒很快就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家里的炕上。
实际上,村里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坐在坟地里的死人排子上,在胡言乱语。
这件事之后,陈俊儒的身体就不行了,我表舅找了一个东北看香的给看看,说陈俊儒是招了狐仙了,不过这狐仙不是来害陈俊儒的,没有坏心。
接下来,陈俊儒就开始信佛,信道,信萨满,家里就没有断了来做法事的。后来陈俊儒总结出来一整套关于灵异方面的东西,干脆就谁也不信了,开始信自己。
陈俊儒最后在这个世上的半年里,一直活得浑浑噩噩,给我讲了很多他的往事,尤其是反反复复讲他和祖母的婚事,讲那天晚上看到的两个老鬼。
他甚至记得那间大院子的任何细节,尤其是说起那些金子的时候,两眼会像金子一样放光。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到了晚上,陈俊儒就会在屋子里和人谈话,我在对屋不想听都能听到,从前到后总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但是有来有回,挺渗人的。村里亲戚告诉我,陈俊儒撞克我祖母了,他这是在和我祖母聊天。
后来,陈俊儒砍了后院的一棵花椒树,弄了个树杈,自己在这树杈上糊了个纸人,还买了假发戴在纸人头上。
每天就用那把乌木梳子给纸人梳头。晚上总是不睡觉,一说就能说一晚上。
接下来的一个月不吃东西,脖子里肿了一个疙瘩,喝水都费劲了,在炕上熬了一个月,没拉也没尿,干干净净死在了我家的热炕上。
我整理遗物的时候,也就没啥值钱的东西了。留下来的两件东西就是那把梳子和那本《地理万山图》。
这《地理万山图》我从不认字的时候就开始翻着看里面的图画。认识字了就开始看里面晦涩难懂的一些古文。
说心里话,那时候我是看得迷迷糊糊,一直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本风水书。
我一般大的小伙伴儿有的去当兵了,有的去上学了。我必须养活自己,勉强上完了初中,然后跟着生产队去修河去了。
我和王虎就是在修河的时候认识的。
王虎是北京人,小名虎子。他成分不好,是个资本家的家庭。家里人为了让王虎有个好前程,就把王虎过继给了滦县的贫农舅舅家,户口这么迁过来,这王虎就也成了光荣的贫农了。
王虎那时候还小,后来逐渐长大了才发现,贫农又有些不吃香了,现在大家又开始追捧万元户了。
修河的时候,我和虎子是一个担子,我俩一前一后抬大筐,从河底往河岸上抬河沙,肩膀都压得红·肿出血,就为了挣那一天块八毛的工资。
一来二去,我和王虎就熟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王虎就抱怨说:“你说我冤不冤,当年要是不把我过继到农村,现在我在京城也分房子了。
我家平反了,按照户口分了房子,哥哥姐姐也都找到了工作,有的当了教师,有的成了工人。就剩我一个在这里修河,我比窦娥都冤。”
我说:“我是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这觉悟就有问题了。”
王虎说:“我觉得我适合当兵保卫祖国,站在祖国的边疆,为人民站好每一班岗。或者我可以当个火车司机,凭什么我就在这里修河啊!修河的人这么多,不差我一个,我更适合有挑战性的岗位。我这颗滚烫的红心在燃烧,你懂么?我急切地想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你懂么?!”
我笑着说:“你就再把户口调回去呗。”
“调动户口哪里那么容易,当初过继给舅舅,可是通过革委会办理的正规手续。城市户口转农村户口容易,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想都别想。我从资本家到了贫农,这才高兴几年啊,现在风向又变了,资本家又吃香了。我想变回去怎么就不行了?谁能给我主持公道!”
说着,王虎愤怒地把铁锹往河底一戳,这一下没戳进去,就听到当的一声响。
我和王虎都愣了一下,王虎用铁锹扒拉了两下,在这河底竟然出现了一块紫黑色的木板。
王虎和我都好奇,开始用铁锹铲去上面的河沙,想不到这木板越清理越大,最后竟然清理出来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
王虎左右看看,小声说:“老陈,别吱声。”
说着就开始埋,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干啥,不过看王虎的样子似乎有什么秘密。埋完了之后,王虎一搂我的肩膀,趴在我耳边小声说:“老陈,别声张。”
“这箱子里有啥啊?挖出来打开看看呀!”我好奇地说。
王虎小声说:“这是一口棺材。”
我想了一下,心说不对啊。我说:“不会,棺材不会这么小。”
“竖着呢,这是发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王虎小声说,“我看了,这棺材是上好的乌木打造,上了九层漆,上面还有花鸟的纹路,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奶奶,搞不好是个清朝格格的棺材。里面肯定有货。”
我半信半疑地说:“不能吧。”
刚好这时候队长过来了,问我俩不干活嘀嘀咕咕干啥呢。
王虎顿时捂着说肚子疼,实在憋不住了,让我拎着棉大衣给他挡着,他这时候解开了裤子,蹲在这里拉了一泡屎。
不远处的大姑娘都躲得远远的,有已婚妇女开始骂他,用土坷垃砸他。
不过这个办法奏效,一直到天黑,也没有人来我和王虎的分段,安全地守护住了这口棺材的秘密。
我们的住宿地点在三里外的大龙沟,干一天活我倒下就睡着了。
我睡得正香,就梦到有一双爪子伸过来抓住了我的脑袋,我吓得一激灵,猛地睁开眼。这时候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说:“老陈,是我,虎子。”
我坐起来,围着棉被小声骂道:“你他妈有病吧,大晚上的不睡觉,你干啥啊!”
“起来,跟我走。”虎子用手电筒给我照着炕上的衣服,顺手把毛衣扔给了我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老陈,今晚过后,也许我俩就发了。快穿上毛衣,哎呦卧槽,你毛衣穿反了……”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