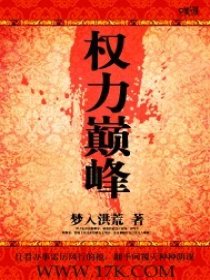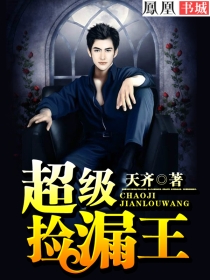第5章 被欺负
阮小沫分配到了一块抹布和一桶清洗用的水桶。
她的工作是负责擦这间房的地板,帝宫的地板都是极其昂贵的材质,所以只能由人来亲手擦拭干净再做保养。
那人吩咐完,就走了。
阮小沫低头盯着自己跟前的一桶水,还有挂在水桶上的抹布,脸上并没有什么神情。
她现在既然不能逃走,也不能找人求救。
靳烈风,是包括阮家在内,所有人都只敢巴结讨好,不敢招惹的存在。
在心底叹了口气,阮小沫蹲下身拿起抹布,在水桶上方拧个半干,起身四下打量一眼,走到一个方向,开始了不甘不愿的打扫。
眼下,她只能先暂时妥协。
“我以为是什么身材好得不得了的大美人,那么自信不会受罚敢给少爷下药呢,原来也不怎么样嘛。”
“别这么说啊,毕竟自知之明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阴阳怪气的调调,一唱一和地在房间里响起。
阮小沫擦地板的动作顿了下,她就知道这两个女人会找茬。
“不出声啊?”一个女人讥笑地走了过来,女佣鞋子在阮小沫的视线里出现:“跟你说话呢,不会是个哑巴吧!”
“哑巴肯定不能啊,不然在少爷和她得多缺少乐趣啊!”另一个女人意有所指地笑着:“不过你还真是太高估自己了,少爷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算计,你现在还好好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了。”
阮小沫漠然地抬头看向她两:“……”
行了,从她被抓到这里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说她幸运奇迹了,她们两能不能换个词?
她又低下头去做事,漠视的态度让两人有一种莫名的受辱感。
虽然都是女佣,但这个居然敢给少爷下药、得罪了少爷的女人明明才是最下等的女佣,有什么资格,又凭什么敢无视她们两?!
“听说和少爷那次是你的第一次?”一个女佣假意走过去关心道:“可惜哟,女人这辈子只有一次都这样献出去了,还是没能成功勾搭到少爷,你肯定很难过吧?”
“就是,女人最宝贵的第一次都没了,你还落得这么个下场,真可怜。”另一个女佣接话,脸上挂着虚伪的安慰:“不过我想你也不在意,毕竟能做出这种事的女人……本身就很不在意这种事吧?”
“听说你还是大小姐,真的假的啊?你爸妈是怎么教出你这么一个为了上位,不惜出卖自己的女——”
“对啊,我确实不在意。”
阮小沫冷冷地出声打断她们的冷嘲热讽,站起身,直视着眼前两个人。
她本来以为只要不搭腔,这两个人感到无趣就会离开的,谁知道她们竟然越说越过分了。
看清楚两人眼底的妒忌之后,她顿时明白了。
靳烈风在外有那么多名媛淑女仰慕着,怎么可能帝宫没有?
可靳烈风对那些有家世有外表的女人尚且挑剔得很,帝宫里爱慕他的女佣哪有机会?
前面说她不在意的女佣,也只是想用这个借口羞辱她而已,完全没想到她居然会直接一口承认,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
阮小沫冷笑着看向那个女佣:“第一次,呵,第一次?这算什么最宝贵的东西?成年人了,这种事很奇怪吗?有什么大不了?”
女佣脸色难看了起来:“哟,你费尽心机对少爷下药的事谁不知道?现在又来装什么云淡风轻啊!”
下药,呵,又提下药。
阮小沫勾了勾唇角,淡淡地回应:“对啊,这种事只要下药就可以做到,你这么想,那也去下啊!”
另一个女佣气急:“阮小沫!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要脸!以为自己能用不要脸的方式上位,活该被少爷嫌弃得要死!”
“发生过一次关系就叫不要脸?那你这辈子可千万别有这样的机会了!你们两是从哪个朝代穿越来的吗?还是棺材板没钉严实,让你这个成了精的牌坊蹦出来了么?”
被人骂做“成了精的牌坊”,挑事的女佣气坏了:“你骂谁牌坊?!”
阮小沫把手里的抹布往水桶里利落地一丢,瞬间溅起来水花给她平添了几分气势。
“除了成了精的牌坊,谁会把这种东西当成‘最宝贵的东西’?还是说,你作为一个人,浑身上下除了那层东西,就没有别的有价值了吗?那么可怜的是你,不是我!”
阮小沫语速不疾不徐,语气平淡,但比起两个女佣气急败坏的模样,一点儿没落下风。
两个女佣被她的话怼得反驳不了,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其中一个甚至直接踢翻了她装水的水桶。
“咚”地一声,哗啦啦的水淌了一地,还有些溅到了阮小沫的裙边鞋子上。
阮小沫无动于衷地看着她们两,冷眼看着那两个挑事的女佣,被她气得一脸毒气攻心的模样。
“真会给自己找借口!”一个女佣鄙夷地看了她一眼:“不就是出卖自己失败了么,所以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咯,懒得跟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扯!对了!不只地板,这里的桌椅板凳所有家具你也都要擦!”
阮小沫本来就还浑身不舒服的,一听到这句话,顿时眼睛瞪圆了:“所有家具?!”
“你忘了你是下等女佣了?帝宫里,谁都能命令你做事知道么!”
两个女佣终于感觉找回一点面子,脸上得意的神色又恢复了些。
两人一起离开房间时,嘴里还嫌弃地道:“歪理可真多,和她待一起我都嫌脏!啧啧!”
房门关上,少了两个人,这间房显得更大了。
阮小沫扶着腰,心情沉痛地四下打量屋内繁多的家具,第一次有一种会因为打扫而累死的觉悟。
也许刚才她不该逞一时口舌之快的……
不过,那两个人走了,房间里倒也清净多了,这也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她蹲下身,把水桶扶正,开始用抹布吸附地上的水挤回桶里。
做着事情,她眼神黯忽然淡了不少。
刚才她说那些话,那么若无其事地样子,其实有一半是为了气那两个女人。
她的工作是负责擦这间房的地板,帝宫的地板都是极其昂贵的材质,所以只能由人来亲手擦拭干净再做保养。
那人吩咐完,就走了。
阮小沫低头盯着自己跟前的一桶水,还有挂在水桶上的抹布,脸上并没有什么神情。
她现在既然不能逃走,也不能找人求救。
靳烈风,是包括阮家在内,所有人都只敢巴结讨好,不敢招惹的存在。
在心底叹了口气,阮小沫蹲下身拿起抹布,在水桶上方拧个半干,起身四下打量一眼,走到一个方向,开始了不甘不愿的打扫。
眼下,她只能先暂时妥协。
“我以为是什么身材好得不得了的大美人,那么自信不会受罚敢给少爷下药呢,原来也不怎么样嘛。”
“别这么说啊,毕竟自知之明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阴阳怪气的调调,一唱一和地在房间里响起。
阮小沫擦地板的动作顿了下,她就知道这两个女人会找茬。
“不出声啊?”一个女人讥笑地走了过来,女佣鞋子在阮小沫的视线里出现:“跟你说话呢,不会是个哑巴吧!”
“哑巴肯定不能啊,不然在少爷和她得多缺少乐趣啊!”另一个女人意有所指地笑着:“不过你还真是太高估自己了,少爷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算计,你现在还好好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了。”
阮小沫漠然地抬头看向她两:“……”
行了,从她被抓到这里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说她幸运奇迹了,她们两能不能换个词?
她又低下头去做事,漠视的态度让两人有一种莫名的受辱感。
虽然都是女佣,但这个居然敢给少爷下药、得罪了少爷的女人明明才是最下等的女佣,有什么资格,又凭什么敢无视她们两?!
“听说和少爷那次是你的第一次?”一个女佣假意走过去关心道:“可惜哟,女人这辈子只有一次都这样献出去了,还是没能成功勾搭到少爷,你肯定很难过吧?”
“就是,女人最宝贵的第一次都没了,你还落得这么个下场,真可怜。”另一个女佣接话,脸上挂着虚伪的安慰:“不过我想你也不在意,毕竟能做出这种事的女人……本身就很不在意这种事吧?”
“听说你还是大小姐,真的假的啊?你爸妈是怎么教出你这么一个为了上位,不惜出卖自己的女——”
“对啊,我确实不在意。”
阮小沫冷冷地出声打断她们的冷嘲热讽,站起身,直视着眼前两个人。
她本来以为只要不搭腔,这两个人感到无趣就会离开的,谁知道她们竟然越说越过分了。
看清楚两人眼底的妒忌之后,她顿时明白了。
靳烈风在外有那么多名媛淑女仰慕着,怎么可能帝宫没有?
可靳烈风对那些有家世有外表的女人尚且挑剔得很,帝宫里爱慕他的女佣哪有机会?
前面说她不在意的女佣,也只是想用这个借口羞辱她而已,完全没想到她居然会直接一口承认,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
阮小沫冷笑着看向那个女佣:“第一次,呵,第一次?这算什么最宝贵的东西?成年人了,这种事很奇怪吗?有什么大不了?”
女佣脸色难看了起来:“哟,你费尽心机对少爷下药的事谁不知道?现在又来装什么云淡风轻啊!”
下药,呵,又提下药。
阮小沫勾了勾唇角,淡淡地回应:“对啊,这种事只要下药就可以做到,你这么想,那也去下啊!”
另一个女佣气急:“阮小沫!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要脸!以为自己能用不要脸的方式上位,活该被少爷嫌弃得要死!”
“发生过一次关系就叫不要脸?那你这辈子可千万别有这样的机会了!你们两是从哪个朝代穿越来的吗?还是棺材板没钉严实,让你这个成了精的牌坊蹦出来了么?”
被人骂做“成了精的牌坊”,挑事的女佣气坏了:“你骂谁牌坊?!”
阮小沫把手里的抹布往水桶里利落地一丢,瞬间溅起来水花给她平添了几分气势。
“除了成了精的牌坊,谁会把这种东西当成‘最宝贵的东西’?还是说,你作为一个人,浑身上下除了那层东西,就没有别的有价值了吗?那么可怜的是你,不是我!”
阮小沫语速不疾不徐,语气平淡,但比起两个女佣气急败坏的模样,一点儿没落下风。
两个女佣被她的话怼得反驳不了,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其中一个甚至直接踢翻了她装水的水桶。
“咚”地一声,哗啦啦的水淌了一地,还有些溅到了阮小沫的裙边鞋子上。
阮小沫无动于衷地看着她们两,冷眼看着那两个挑事的女佣,被她气得一脸毒气攻心的模样。
“真会给自己找借口!”一个女佣鄙夷地看了她一眼:“不就是出卖自己失败了么,所以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咯,懒得跟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扯!对了!不只地板,这里的桌椅板凳所有家具你也都要擦!”
阮小沫本来就还浑身不舒服的,一听到这句话,顿时眼睛瞪圆了:“所有家具?!”
“你忘了你是下等女佣了?帝宫里,谁都能命令你做事知道么!”
两个女佣终于感觉找回一点面子,脸上得意的神色又恢复了些。
两人一起离开房间时,嘴里还嫌弃地道:“歪理可真多,和她待一起我都嫌脏!啧啧!”
房门关上,少了两个人,这间房显得更大了。
阮小沫扶着腰,心情沉痛地四下打量屋内繁多的家具,第一次有一种会因为打扫而累死的觉悟。
也许刚才她不该逞一时口舌之快的……
不过,那两个人走了,房间里倒也清净多了,这也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她蹲下身,把水桶扶正,开始用抹布吸附地上的水挤回桶里。
做着事情,她眼神黯忽然淡了不少。
刚才她说那些话,那么若无其事地样子,其实有一半是为了气那两个女人。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