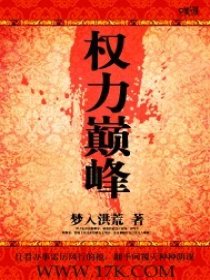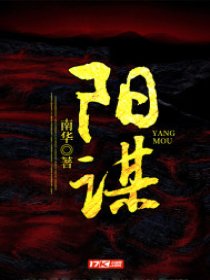第十六章 人心这个东西
这简直是牛鬼蛇神的聚会场,一个小型的迪吧。
屋里的窗帘全被被拉了起来,啤酒味混合着烟味和一些不知名的味道,彻耳的躁动音中有人正在摇头甩尾蹦的欢快,蓝的绿的红的光四处扫射,如果不是宋福理智还在,他会觉得这是个蹦迪吧,而不是居民区,这都没人报警?他拧着眉,看似和煦的脸上存了几分不爽。
听惯了咖啡馆轻音乐的熏陶,春妮一听到屋内的声音就掩住了耳朵,下一秒又觉得不妥,把站在最前的老太太拽了过来,双手掩住了她的耳朵。
房门被开,有人进来,里面正在狂欢的人却没有一个注意到,春妮注意到来太太浑身颤抖,几次三番想冲上去,但被春妮拽着,她只能无助的拍着膝盖跺着脚大喊:“别跳了,别跳了呀,这是家里啊,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笑笑,笑笑你在哪儿呀!”
她看到人群中的孙子和孙女,情绪更加奔溃了:“薇薇轩轩,你们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快点停下呀!”
但她的外孙和外孙女没有注意到她,他们正高举着双手,闭着眼睛,在摇头晃脑中享受极致的欢愉。
忽然之间,万籁俱寂。
宋福找到了音响,摁了开关。
“奶奶的,终于清静了。”宋福松了口气,掏了掏耳朵。
“谁啊,哪个神经病关的!”五颜六色的昏暗中,有人大骂了一声。
春妮摸索到了门口的开关,“啪”的一声,房子里的灯亮了。
屋子里至少有十多个人,都是看起来刚成年不久的孩子,一些站着,一些瘫着,还有几个穿着鞋子站在沙发上。
“妈的,什么东西?”有个梳着脏辫的男生说话了,他的目光看到门口的人,一脸不悦:“外婆,你开灯干嘛!扫兴不扫兴啊!”
正是陈笑的儿子,秦轩。
站在春妮身边的老太太忽然尖叫了一声,她蹒跚着冲了过去,扑打着站在沙发上的那几个孩子:“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这是我闺女亲手洗的,你们……你们怎么能穿着鞋子踩!”
那原本打理的干干净净沙发上,此刻全是肮脏的脚印,上面甚至还丢着烟头和喝完的啤酒瓶,老太太心疼万分的看着被烟头烫出来的破洞,不知道是气的还是难过的,一个劲的用手拍着沙发。
“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我闺女辛辛苦苦打理的……”她一边清理一边哭。
春妮看的眼睛都发酸了。
几个一脸茫然的年轻人小声问着:“这谁?”
秦轩不远处站着个染着粉色头发的女生,此时她一脸不悦的瞪了老太太一眼:“外婆,你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好不容易聚一块儿呢,你要是没事就赶紧回去吧行不行?还有,你带来的这都是谁?”
正是陈笑的女儿,秦薇。
她扫了一圈,看到春妮时还一脸敌意,看到站在音响旁边的宋福时却忽然亮了眼睛,很显然宋福的长相很符合她的审美。
春妮站在门口,下意识的拨通了陈笑的电话。
铃声乍然响起,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是从卧室传出来的。
宋福和春妮的眼神只在空中交汇了一瞬,下一刻,就见两人如风一般朝着那个房间冲了过去。
拧开房门,宋福急速冲击的身体一个紧急刹车但没刹住,跳起脚来跨了个大步子,喊了一声:“小心!”
紧随其后的春妮扶住门框,看到距离门口不远的地上有一滩破碎的玻璃。
“陈女士!”宋福焦急的声音传来,春妮心里哐当一声,越过那一滩玻璃跑了过去,她一下子跪坐在陈笑身边,看着宋福的动作,迅速的拨打了120。
老太太第三个冲进来,她根本没注意到那些玻璃渣,就那么踩了上去,朝着女儿的方向奔去。
“笑笑!我的笑笑!”她恸哭出声。
那些年轻的孩子以秦轩和秦薇为首守在门口,他们窃窃私语:“秦轩,秦薇,你们妈妈是不是出事了?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家里还有你们妈妈啊,这不会真的……”
“哎呀,能有什么事儿!”秦轩满不在乎地说道:“我妈她经常这样,就是吓唬我们的,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不信你们看,很快她就醒了!”
秦薇却皱着眉头,她扯了扯秦轩的衣角:“我怎么觉得不对啊,妈今天不应该去给二舅爷过生日去了吗?”
“跟爸吵架了呗。”秦轩依旧一脸无所谓。
那一边,宋福掐着陈笑的人中,眼见怀里的人终于有了点动静,他终于松了口气,连带着春妮也塌了肩膀。
老太太拍着心口长长的呼了口气,向后一跌坐在了地上,怔怔的说不出话来,只是眼泪一个劲的往出来淌。
“我们现在不敢轻举妄动。”宋福抬头看向春妮:“陆医生他们到哪儿了?”
进门之前,春妮接到了季茫的电话,对方表示自己和陆宴那边已经结束,已经在赶来陈笑家的路上。
“快了,我打了距离我们最近的慈恩医院的120,宋福……”春妮的声音里充满担忧,并没有把话说完,她知道宋福明白。
宋福额角冒出细密的汗珠,默默叹了口气,心里也有点吃不准。
就在这个时候,宋福听到了一道低沉的男声叫他的名字,他心里重重的松了口气,仿佛这声音救他于水火之中,简直是如沐春风。
陆宴和季茫先于救护车到了。
他们同样紧蹙着眉,穿过客厅的一片狼藉来到卧室,看到宋福他们,陆宴眉头皱的更深了点:“怎么回事?”
他说着这话,蹲在了春妮身边,动作比话还要快,已经在检查陈笑的情况了。
“还好,只是晕倒了。”陆宴的声音平稳的传了出来:“救护车到了,直接送到疗养院。”
宋福和春妮略显诧异,看了陆宴一眼。
站在门口的秦轩此时开口了,他耸了耸肩:“看吧,我就说没事。”
可秦薇还是觉得哪里不对。
就在她还在想着的时候,老太太终于回过神了,她有些笨拙地撑着床沿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向着她疼爱了快二十年的孙子和孙女走过去,她的脚再次踩上那一滩碎玻璃,旧鞋子的鞋底已经被磨的很平了,玻璃从鞋底扎进她的脚心,但她丝毫感觉不到疼。
她眼里含着泪,嘴角颤抖着,极其失望地盯着这两个如花朵一般的孩子,然后抬起胳膊,一巴掌重重的打到了外孙的脸上。
一巴掌下去,打麻了老太太的手,也打懵了秦轩的脑子。
他不可置信的捂着脸:“你有病啊!你打我干嘛!”
话音刚落,老太太咬着牙,又是一巴掌打了过来:“那是我女儿,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的孩子啊!”
她指着秦轩,食指用力的戳着他的心口:“你们是她的孩子!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生你的时候她大出血,差点死了!还有你!”
她反过来指着秦薇:“生你的时候她顺转剖,怕伤着你,麻药都不敢用!为了你们,她鬼门关走了,地狱也下了!你们怎么对我的孩子的,啊?她病了,癌啊,癌症啊,活不了多久了,你们还要这么送她一程吗,啊?怕她多活两天吗,啊?”
老太太捶打着心口,她浑身颤抖:“没良心,你们没良心啊!”
两个孩子彻底懵了。
“外婆……”秦薇终于回过点神来:“你说谁,谁得了癌症?”
老太太没有回答她,倒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传进了她的耳朵。
季茫站起来走到老太太身边,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冷漠地看着这两个孩子:“你妈妈,陈笑,癌症,活不了多久了,这么说,听得懂吗?”
陆宴询声抬头,看了季茫一眼。
救护车的声音响起,春妮跑出去接应。
季茫低头,看着老太太走过的地方沾染上血迹,眉头皱了皱。
春妮很快带着人上来,陈笑被抬上担架,站在这个房子里的人都自觉的让开地方,秦轩和秦薇愣愣的,他们茫然地看着妈妈被抬走,脑子里还不断回旋着癌症,活不久了这样的字眼。
“怎么可能?”秦薇戚戚地看向秦轩:“不就是晕倒吗?”
秦轩没有搭话,他低着头,目光盯着脚尖,不知道在想什么。
纵然初次见面,但季茫对这两个孩子实在没有什么好感。
纵然陈笑对孩子的教育是错误的,但他们成年了,不是小孩子了,不是吗?
一同享受欢愉和热闹的朋友们,随着担架抬出陈笑的时候,他们悄无声息又迅速的离开了这一方欢乐场。
秦轩忽然转身跑了出去,但这个时候,没人会在意他。
季茫扶着老太太,侧头叫陆宴:“陆医生,你能帮忙处理一下吗?”
短短的时间内,她先后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因为母亲的离开而伤了脚,另一个,是为了女儿,忘却了自身的痛苦,季茫觉得,人心这个东西,放到谁身上都是另一番景象。
屋里的窗帘全被被拉了起来,啤酒味混合着烟味和一些不知名的味道,彻耳的躁动音中有人正在摇头甩尾蹦的欢快,蓝的绿的红的光四处扫射,如果不是宋福理智还在,他会觉得这是个蹦迪吧,而不是居民区,这都没人报警?他拧着眉,看似和煦的脸上存了几分不爽。
听惯了咖啡馆轻音乐的熏陶,春妮一听到屋内的声音就掩住了耳朵,下一秒又觉得不妥,把站在最前的老太太拽了过来,双手掩住了她的耳朵。
房门被开,有人进来,里面正在狂欢的人却没有一个注意到,春妮注意到来太太浑身颤抖,几次三番想冲上去,但被春妮拽着,她只能无助的拍着膝盖跺着脚大喊:“别跳了,别跳了呀,这是家里啊,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笑笑,笑笑你在哪儿呀!”
她看到人群中的孙子和孙女,情绪更加奔溃了:“薇薇轩轩,你们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快点停下呀!”
但她的外孙和外孙女没有注意到她,他们正高举着双手,闭着眼睛,在摇头晃脑中享受极致的欢愉。
忽然之间,万籁俱寂。
宋福找到了音响,摁了开关。
“奶奶的,终于清静了。”宋福松了口气,掏了掏耳朵。
“谁啊,哪个神经病关的!”五颜六色的昏暗中,有人大骂了一声。
春妮摸索到了门口的开关,“啪”的一声,房子里的灯亮了。
屋子里至少有十多个人,都是看起来刚成年不久的孩子,一些站着,一些瘫着,还有几个穿着鞋子站在沙发上。
“妈的,什么东西?”有个梳着脏辫的男生说话了,他的目光看到门口的人,一脸不悦:“外婆,你开灯干嘛!扫兴不扫兴啊!”
正是陈笑的儿子,秦轩。
站在春妮身边的老太太忽然尖叫了一声,她蹒跚着冲了过去,扑打着站在沙发上的那几个孩子:“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这是我闺女亲手洗的,你们……你们怎么能穿着鞋子踩!”
那原本打理的干干净净沙发上,此刻全是肮脏的脚印,上面甚至还丢着烟头和喝完的啤酒瓶,老太太心疼万分的看着被烟头烫出来的破洞,不知道是气的还是难过的,一个劲的用手拍着沙发。
“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我闺女辛辛苦苦打理的……”她一边清理一边哭。
春妮看的眼睛都发酸了。
几个一脸茫然的年轻人小声问着:“这谁?”
秦轩不远处站着个染着粉色头发的女生,此时她一脸不悦的瞪了老太太一眼:“外婆,你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好不容易聚一块儿呢,你要是没事就赶紧回去吧行不行?还有,你带来的这都是谁?”
正是陈笑的女儿,秦薇。
她扫了一圈,看到春妮时还一脸敌意,看到站在音响旁边的宋福时却忽然亮了眼睛,很显然宋福的长相很符合她的审美。
春妮站在门口,下意识的拨通了陈笑的电话。
铃声乍然响起,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是从卧室传出来的。
宋福和春妮的眼神只在空中交汇了一瞬,下一刻,就见两人如风一般朝着那个房间冲了过去。
拧开房门,宋福急速冲击的身体一个紧急刹车但没刹住,跳起脚来跨了个大步子,喊了一声:“小心!”
紧随其后的春妮扶住门框,看到距离门口不远的地上有一滩破碎的玻璃。
“陈女士!”宋福焦急的声音传来,春妮心里哐当一声,越过那一滩玻璃跑了过去,她一下子跪坐在陈笑身边,看着宋福的动作,迅速的拨打了120。
老太太第三个冲进来,她根本没注意到那些玻璃渣,就那么踩了上去,朝着女儿的方向奔去。
“笑笑!我的笑笑!”她恸哭出声。
那些年轻的孩子以秦轩和秦薇为首守在门口,他们窃窃私语:“秦轩,秦薇,你们妈妈是不是出事了?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家里还有你们妈妈啊,这不会真的……”
“哎呀,能有什么事儿!”秦轩满不在乎地说道:“我妈她经常这样,就是吓唬我们的,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不信你们看,很快她就醒了!”
秦薇却皱着眉头,她扯了扯秦轩的衣角:“我怎么觉得不对啊,妈今天不应该去给二舅爷过生日去了吗?”
“跟爸吵架了呗。”秦轩依旧一脸无所谓。
那一边,宋福掐着陈笑的人中,眼见怀里的人终于有了点动静,他终于松了口气,连带着春妮也塌了肩膀。
老太太拍着心口长长的呼了口气,向后一跌坐在了地上,怔怔的说不出话来,只是眼泪一个劲的往出来淌。
“我们现在不敢轻举妄动。”宋福抬头看向春妮:“陆医生他们到哪儿了?”
进门之前,春妮接到了季茫的电话,对方表示自己和陆宴那边已经结束,已经在赶来陈笑家的路上。
“快了,我打了距离我们最近的慈恩医院的120,宋福……”春妮的声音里充满担忧,并没有把话说完,她知道宋福明白。
宋福额角冒出细密的汗珠,默默叹了口气,心里也有点吃不准。
就在这个时候,宋福听到了一道低沉的男声叫他的名字,他心里重重的松了口气,仿佛这声音救他于水火之中,简直是如沐春风。
陆宴和季茫先于救护车到了。
他们同样紧蹙着眉,穿过客厅的一片狼藉来到卧室,看到宋福他们,陆宴眉头皱的更深了点:“怎么回事?”
他说着这话,蹲在了春妮身边,动作比话还要快,已经在检查陈笑的情况了。
“还好,只是晕倒了。”陆宴的声音平稳的传了出来:“救护车到了,直接送到疗养院。”
宋福和春妮略显诧异,看了陆宴一眼。
站在门口的秦轩此时开口了,他耸了耸肩:“看吧,我就说没事。”
可秦薇还是觉得哪里不对。
就在她还在想着的时候,老太太终于回过神了,她有些笨拙地撑着床沿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向着她疼爱了快二十年的孙子和孙女走过去,她的脚再次踩上那一滩碎玻璃,旧鞋子的鞋底已经被磨的很平了,玻璃从鞋底扎进她的脚心,但她丝毫感觉不到疼。
她眼里含着泪,嘴角颤抖着,极其失望地盯着这两个如花朵一般的孩子,然后抬起胳膊,一巴掌重重的打到了外孙的脸上。
一巴掌下去,打麻了老太太的手,也打懵了秦轩的脑子。
他不可置信的捂着脸:“你有病啊!你打我干嘛!”
话音刚落,老太太咬着牙,又是一巴掌打了过来:“那是我女儿,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的孩子啊!”
她指着秦轩,食指用力的戳着他的心口:“你们是她的孩子!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生你的时候她大出血,差点死了!还有你!”
她反过来指着秦薇:“生你的时候她顺转剖,怕伤着你,麻药都不敢用!为了你们,她鬼门关走了,地狱也下了!你们怎么对我的孩子的,啊?她病了,癌啊,癌症啊,活不了多久了,你们还要这么送她一程吗,啊?怕她多活两天吗,啊?”
老太太捶打着心口,她浑身颤抖:“没良心,你们没良心啊!”
两个孩子彻底懵了。
“外婆……”秦薇终于回过点神来:“你说谁,谁得了癌症?”
老太太没有回答她,倒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传进了她的耳朵。
季茫站起来走到老太太身边,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冷漠地看着这两个孩子:“你妈妈,陈笑,癌症,活不了多久了,这么说,听得懂吗?”
陆宴询声抬头,看了季茫一眼。
救护车的声音响起,春妮跑出去接应。
季茫低头,看着老太太走过的地方沾染上血迹,眉头皱了皱。
春妮很快带着人上来,陈笑被抬上担架,站在这个房子里的人都自觉的让开地方,秦轩和秦薇愣愣的,他们茫然地看着妈妈被抬走,脑子里还不断回旋着癌症,活不久了这样的字眼。
“怎么可能?”秦薇戚戚地看向秦轩:“不就是晕倒吗?”
秦轩没有搭话,他低着头,目光盯着脚尖,不知道在想什么。
纵然初次见面,但季茫对这两个孩子实在没有什么好感。
纵然陈笑对孩子的教育是错误的,但他们成年了,不是小孩子了,不是吗?
一同享受欢愉和热闹的朋友们,随着担架抬出陈笑的时候,他们悄无声息又迅速的离开了这一方欢乐场。
秦轩忽然转身跑了出去,但这个时候,没人会在意他。
季茫扶着老太太,侧头叫陆宴:“陆医生,你能帮忙处理一下吗?”
短短的时间内,她先后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因为母亲的离开而伤了脚,另一个,是为了女儿,忘却了自身的痛苦,季茫觉得,人心这个东西,放到谁身上都是另一番景象。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