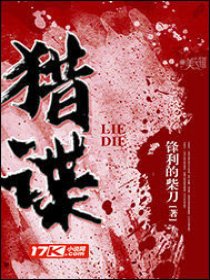:第二章
张来福见到沈喜宝,油然涌起同病相怜之情。
两人倚着树面对面聊开了天。沈喜宝兜里揣着一包便宜香烟,两个人“嗞嗞”地抽着。
沈喜宝说他当初从师傅家跑回去复读,师傅嘲笑他榆木脑袋,木匠都学不好还想考大学,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其实他不是学不好木匠,而是师傅太抠门,开头一两年徒弟只是为他做家务,洗衣喂猪带孩子甚至倒尿壶样样都干,在客户和工地上顶多让你削削树皮,拉拉大锯,磨磨斧头刨凿,到第三年才正式教手艺,而且出师后还要替他白干上一年,他就受不了了。
想不到复读后果真年年不中,现在父母要他再去师傅那里学完木匠,他哪里有脸去?也不愿意去。
他父母身体都不好,上学是三个姐姐供的。得知他今年又落榜,陆家荡的大姐夫过来有事时指责他二十几岁的大男人了,既然考学不行,不学手艺怎么办,难道靠父母和姐姐们供一世?他实在不能面对家人和亲戚的脸色和责怪,只好出来放鹅,带上干粮,早出晚归,眼不见心不烦。
说完,从旁边帆布书包里拿出一块米饼来,递给张来福:
“呶,尝尝!”
张来福本想不接的,他不能吃这米糁子烙的饼,吃了吐酸水。但又怕拂了他的好意,接过来用手一点一点掰了往嘴里放。沈喜宝哂笑:
“倒底是校长家的公子,吃个饼都这么斯文!”
张来福啼笑皆非,也不解释,倒想起自己的奶奶来了。
因为小时候奶奶就曾经夸过他吃饼斯文——两种“斯文”却不是一回事儿。
小时候在大集体,家家都穷,生产队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
新麦分下来,家里大部分用来磨成糁子熬粥喝,和炒制成焦屑,只留下一二十斤,来了亲戚朋友用来换面条待客,偶尔也到街上换几只烧饼解解馋。一斤小麦换六个烧饼,都是早饭前让张来福去换。
张来福最喜欢吃烧饼,特别是刚出炉的烧饼脆崩崩的,焦香扑鼻,勾得他馋涎欲滴!但父亲规矩大,要回家就着稀粥吃。
他只得在回家的途中把烧饼边缘一点硬疤子掰下来吃,这样不影响烧饼的整体形状。
到了家,一人分得一只烧饼,他先吃烧饼底子,再吃烧饼肉子,最后才吃洒满芝麻的烧饼面子,这并不是奶奶夸的“斯文”,而是把最好吃的部分留到最后,也是为了延长享受烧饼的过程。
他吃油条也是这样,先一撕为二,再一条一条地吃,这样吃一根油条就好像吃两根油条了。
即便张来福是个宠儿,但家里该跟他上规矩的地方还是不含糊的,这是在真正的爱他,一个不晓得上规矩的人将来走上社会上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是要被人嫌弃的。
吃烧饼张来福不呕酸水,但米饼就不行,他自己也不懂其中的道理。
张来福吃了半块米饼便不吃了,问沈喜宝既然不想学木匠,下面打算做什么。
“我还没有想好,心里乱得很。”沈喜宝叹了口气,“先躲在这里放几天鹅,正好安静安静。”
“那我就来陪你放羊!”张来福笑道。
“你倒不晓得愁。”沈喜宝乜了他一眼,问:“我不明白,你这个从小聪明的人,怎么也考两年都考不上?”
“头一年考不上我不怪自己,复读这一年确实是我自己荒(废)掉的。”张来福拎弄着一根狗尾巴草,略带悔意地说。
“怎么荒掉的?”
“县城里好玩啊,有球打,有冰溜,有电影录相看……总之,我把头玩昏了,等反应过来,就迟了。要不,只要稍微上点紧,考个大专还是不费事的。”
“你今年差多少?”
“差十七分,比去年还退步了。”
“嗐,差十七分算什么差?我差三十七分呢!你基础这么好,应该继续复读的。你才二十岁呀,家里又支持你上,不像我二十四了,‘众叛亲离’的,没有退路了。”沈喜宝诚恳地说。
“我不想上了。”张来福摇摇头。
“你不上,叫你爸爸脸往哪儿搁?他是个校长,不像我爸爸是农民。”
“他要面子,我也有尊严,要我上‘高五’没门儿——考上了都不叫本事!”
“那你想好下面做什么了吗?”
“我正在想。”张来福说,“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于是就一起动脑筋。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养活自己才能摆脱父母的束缚,创业自立是摆在眼前的当务之急。
他们设想了开船搞运输,办养鸡场、养猪场,或者承包鱼塘、窑厂好多种发财致富的方法。
但他们没有运输船,就是有船也不会开;办养鸡场养猪场、承包鱼塘窑厂也是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
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其实是赤手空拳,做什么都有心无力!
两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除非……我们出去……”
过了好长时间,张福来突然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沈喜宝没听清楚,问。
“我说,除非我们出去。”
“出去——上哪儿去?”
“走江湖啊!”张来福提高声音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进城打工去,等有了钱再创业,当老板,当企业家。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份杂志,说广东那边青年人白手起家的多哩!”
沈喜宝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却嗫嚅道:
“你不是说我们到广东去打工吧?”
“哪要跑那么远!全国多少好地方,未必非要去广东。”
“最远,也不能出江苏。”沈喜宝轻声说。
“那你同意一起出去了?”
“不出去又怎么办呢!”
“那我们来合计合计,到哪个城市比较合适!”
就像满天乌云裂开一道罅隙,射出金色炫亮的阳光,两个人顿时激动起来,脑筋里翻滚着一个个城市名称——权衡,比对……
炎热的午后,正是农村人歇晌的时分,村庄静谧,田野无人,耳边唯有断续的枯燥蝉鸣。
张来福突然眉毛一扬,正想说什么,树林南面突然鼓噪一片——鹅群“嘎嘎”,羊声“咩咩”。
两个人专注谈事、想事,没注意鹅儿羊儿已寻着嫩草离开他们的视线。难道树林里蹿进几只凶狗,或者闯入一帮舞棒弄棍的顽童?不约而同地,他们站起来撒腿朝那边奔去。
两人倚着树面对面聊开了天。沈喜宝兜里揣着一包便宜香烟,两个人“嗞嗞”地抽着。
沈喜宝说他当初从师傅家跑回去复读,师傅嘲笑他榆木脑袋,木匠都学不好还想考大学,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其实他不是学不好木匠,而是师傅太抠门,开头一两年徒弟只是为他做家务,洗衣喂猪带孩子甚至倒尿壶样样都干,在客户和工地上顶多让你削削树皮,拉拉大锯,磨磨斧头刨凿,到第三年才正式教手艺,而且出师后还要替他白干上一年,他就受不了了。
想不到复读后果真年年不中,现在父母要他再去师傅那里学完木匠,他哪里有脸去?也不愿意去。
他父母身体都不好,上学是三个姐姐供的。得知他今年又落榜,陆家荡的大姐夫过来有事时指责他二十几岁的大男人了,既然考学不行,不学手艺怎么办,难道靠父母和姐姐们供一世?他实在不能面对家人和亲戚的脸色和责怪,只好出来放鹅,带上干粮,早出晚归,眼不见心不烦。
说完,从旁边帆布书包里拿出一块米饼来,递给张来福:
“呶,尝尝!”
张来福本想不接的,他不能吃这米糁子烙的饼,吃了吐酸水。但又怕拂了他的好意,接过来用手一点一点掰了往嘴里放。沈喜宝哂笑:
“倒底是校长家的公子,吃个饼都这么斯文!”
张来福啼笑皆非,也不解释,倒想起自己的奶奶来了。
因为小时候奶奶就曾经夸过他吃饼斯文——两种“斯文”却不是一回事儿。
小时候在大集体,家家都穷,生产队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
新麦分下来,家里大部分用来磨成糁子熬粥喝,和炒制成焦屑,只留下一二十斤,来了亲戚朋友用来换面条待客,偶尔也到街上换几只烧饼解解馋。一斤小麦换六个烧饼,都是早饭前让张来福去换。
张来福最喜欢吃烧饼,特别是刚出炉的烧饼脆崩崩的,焦香扑鼻,勾得他馋涎欲滴!但父亲规矩大,要回家就着稀粥吃。
他只得在回家的途中把烧饼边缘一点硬疤子掰下来吃,这样不影响烧饼的整体形状。
到了家,一人分得一只烧饼,他先吃烧饼底子,再吃烧饼肉子,最后才吃洒满芝麻的烧饼面子,这并不是奶奶夸的“斯文”,而是把最好吃的部分留到最后,也是为了延长享受烧饼的过程。
他吃油条也是这样,先一撕为二,再一条一条地吃,这样吃一根油条就好像吃两根油条了。
即便张来福是个宠儿,但家里该跟他上规矩的地方还是不含糊的,这是在真正的爱他,一个不晓得上规矩的人将来走上社会上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是要被人嫌弃的。
吃烧饼张来福不呕酸水,但米饼就不行,他自己也不懂其中的道理。
张来福吃了半块米饼便不吃了,问沈喜宝既然不想学木匠,下面打算做什么。
“我还没有想好,心里乱得很。”沈喜宝叹了口气,“先躲在这里放几天鹅,正好安静安静。”
“那我就来陪你放羊!”张来福笑道。
“你倒不晓得愁。”沈喜宝乜了他一眼,问:“我不明白,你这个从小聪明的人,怎么也考两年都考不上?”
“头一年考不上我不怪自己,复读这一年确实是我自己荒(废)掉的。”张来福拎弄着一根狗尾巴草,略带悔意地说。
“怎么荒掉的?”
“县城里好玩啊,有球打,有冰溜,有电影录相看……总之,我把头玩昏了,等反应过来,就迟了。要不,只要稍微上点紧,考个大专还是不费事的。”
“你今年差多少?”
“差十七分,比去年还退步了。”
“嗐,差十七分算什么差?我差三十七分呢!你基础这么好,应该继续复读的。你才二十岁呀,家里又支持你上,不像我二十四了,‘众叛亲离’的,没有退路了。”沈喜宝诚恳地说。
“我不想上了。”张来福摇摇头。
“你不上,叫你爸爸脸往哪儿搁?他是个校长,不像我爸爸是农民。”
“他要面子,我也有尊严,要我上‘高五’没门儿——考上了都不叫本事!”
“那你想好下面做什么了吗?”
“我正在想。”张来福说,“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于是就一起动脑筋。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养活自己才能摆脱父母的束缚,创业自立是摆在眼前的当务之急。
他们设想了开船搞运输,办养鸡场、养猪场,或者承包鱼塘、窑厂好多种发财致富的方法。
但他们没有运输船,就是有船也不会开;办养鸡场养猪场、承包鱼塘窑厂也是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
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其实是赤手空拳,做什么都有心无力!
两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除非……我们出去……”
过了好长时间,张福来突然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沈喜宝没听清楚,问。
“我说,除非我们出去。”
“出去——上哪儿去?”
“走江湖啊!”张来福提高声音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进城打工去,等有了钱再创业,当老板,当企业家。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份杂志,说广东那边青年人白手起家的多哩!”
沈喜宝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却嗫嚅道:
“你不是说我们到广东去打工吧?”
“哪要跑那么远!全国多少好地方,未必非要去广东。”
“最远,也不能出江苏。”沈喜宝轻声说。
“那你同意一起出去了?”
“不出去又怎么办呢!”
“那我们来合计合计,到哪个城市比较合适!”
就像满天乌云裂开一道罅隙,射出金色炫亮的阳光,两个人顿时激动起来,脑筋里翻滚着一个个城市名称——权衡,比对……
炎热的午后,正是农村人歇晌的时分,村庄静谧,田野无人,耳边唯有断续的枯燥蝉鸣。
张来福突然眉毛一扬,正想说什么,树林南面突然鼓噪一片——鹅群“嘎嘎”,羊声“咩咩”。
两个人专注谈事、想事,没注意鹅儿羊儿已寻着嫩草离开他们的视线。难道树林里蹿进几只凶狗,或者闯入一帮舞棒弄棍的顽童?不约而同地,他们站起来撒腿朝那边奔去。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